暗影(短篇小说)
暗影(短篇小说)
一
最近我很忙,忙着永远也忙不完的琐碎工作;忙着永远也赴不完的大小聚会及酒宴;忙着在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内心世界里幻想并推演众多不着边际的事儿……当然,我最乐此不疲的,莫过于忙着在朋友圈里变着花样晒这晒那……

朋友圈有着各色人生。几乎每一个喜欢在这个方寸田园里晒这晒那的人,都把朋友圈当作了七彩人生的云存储——或者都把朋友圈当作了可以放飞自我和可以慰藉心灵的小世界。换一种说法,所有忙着在朋友圈里晒这晒那的人,都有其乐此不疲的深层次原因。
我也不例外。
我是一个从小就对异性特别敏感——只要是漂亮女人就都喜欢的博爱型男人。我忙着在朋友圈里晒着晒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也最隐秘的原因,是为了吸引异性的目光和注意力。
准确点说,是为了吸引一个名叫刘欣的漂亮女人的目光和注意力。
二
在我的朋友圈里,最火的人莫过于刘欣了。
我关注她已经很久很久了。但加她为微信好友,却是最近几天的事。
“您的演讲实在太精彩了。听了您的讲座,让人感觉似乎从灵魂里飞出了一道彩虹——为人指点迷津,激发人昂扬奋进……”这是我申请加刘欣为微信好友时所写的话。
加微信好友的申请有着严格的字数限制。因此,不要小看这短短几十个字,它们是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大半天才写出来的。
足足过了两天,刘欣才通过了我的微信好友申请。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撩妹的水平挺高嘛,看了你写的话,应该没有几个女人可以拒绝你吧……长长的省略号后边是一个“坏笑”的图标。
用“欣喜若狂”这几个字来形容我收到刘欣这条信息时的那种状况再恰当不过。从来没有哼唱歌曲习惯的我,竟然情不自禁独自对着镜子哼唱起了“妹妹你大大地往前走,往前走……”之类的曲调。
但冷静下来之后,我的思维回归了理性。
“刘欣老师,我对您的钦佩完全发自内心。您太了不起了。在我们心中,您是女神般的存在,我等凡俗之人岂敢对您有非分之想?加您的微信,一是源于对您的敬佩,二是真心想向您取经,真心把您当作了学习的楷模……”我的回复依然文绉绉的。
这是我的刻意所为。与异性交往,我自以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水平。归根结底,就是懂得把这些女人分成不同种类型,然后视情况“对症下药”——对不同类型的女人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进而用“艺术”的手法捕获她们的心。
刘欣属于已被贴上了“成功人士”标签的那类女人,她们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享有一定的声誉,如今在事业方面更是一路高歌,混得顺风顺水。这类女人有着明显的心理优越感,在她春风得意之时,哪有闲心来理睬一般的人呢?如果按照常规出牌,定然会碰壁。对这种类型女人的心理,我把捏得比较准。她们越是高高在上,内心越是孤寂难耐。因为大部分人对她们都是“敬而远之”。表面上,围着她们转的人很多,但真正能与她们进行心灵交流的人少之又少。换一种说法,“高处不胜寒”的她们,其实很渴望一份心灵的慰藉。当然,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是一个身份地位都与之相“匹配”的男人。
三
初次见到刘欣是在两年前的城区作协年会上。酒到正酣时,外号叫“郭大侠”的作协郭主席满面红光地拿着话题跑到台上,用极其夸张的口吻激奋地说:“我们城区的作家朋友们有福了,刚刚接到消息,说是市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名歌手——大美女刘欣老师百忙中前来为大家捧场,并将即兴为大家献唱一首……”
“郭大侠”话音未落,一阵热烈的掌声突然响起,所有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起身望向大门入口处,只见一位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的高挑女子满脸微笑,迈着轻盈的步子朝我们款款走来。
“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歌星大美女刘欣老师莅临我们的城区作协年会的会场!”郭大侠健步上前,极其绅士屈膝弯腰,然后优雅地朝那黑衣女子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在大美女刘欣接过话筒,说出“作家朋友们好”的那一瞬间,一个记忆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影条件反射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与眼前刘欣的倩影交错甚至重叠在一起。准确点说,是一道暗影越过时空的距离,飘晃到我眼前,直击着我脆弱而善感的神经——眼前这个被称为刘欣的大美女不就是我二十年前在深圳飞西村所认识的那个贵州女孩刘小琴吗?
我惊愕到了极点。
整场晚宴,我都处于混混沌沌之中。直到刘欣唱完了几首歌,并在众人的簇拥之下风光地离开,我才意识到了一点什么。我开始不懈余力地向几乎所有熟识的人打听刘欣的情况,可得到的消息是——刘欣是湖南人,洗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众多音乐大赛的大奖获得者,业内颇有名气的当红歌手。似乎所有的佐证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个风光无限的大美女刘欣根本就不是我当年所认识的那个贵州女孩刘小琴。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不知何故,至那以后,我对刘欣多了份莫名的关注。
关注归关注,我真正动心思主动接近刘欣却是最近的事。
那天,我应邀参加一个“礼仪文化进校园”主题讲座活动,活动的主讲嘉宾就是“市礼仪文化推进讲师团”团长刘欣。在长达三个小时的礼仪文化宣讲中,刘欣多次穿插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借以强调礼仪文化对促进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不知何故,我再次有了两年前初见刘欣时的那种感觉:一道道暗影越过时空的距离,飘晃到我眼前,直击着我脆弱而善感的神经,在一阵阵莫名的雀跃之后,我总要不自觉地把眼前的刘欣和那个贵州女孩刘小琴联系到一起。特别是后来,刘欣几次在演讲中提到她在考上冼星海音乐学院之前,曾独自坚持每天在深圳的一间出租屋里练两小时歌的往事。虽然她并未提及当初在深圳漂泊时所在的具体地方,但我隐隐觉得,她的那段经历似乎与贵州女孩刘小琴当初在深圳的生活轨迹有着明显的重合。
四
我与刘小琴的认识纯属偶然。那是我在深圳流浪的第三个年头,落魄至极的我租住在与飞西村只有一路相隔的横岭塘某栋小阁楼里。那段时间,我白天睡觉,晚上码字,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自由撰稿人的梦。每每弹尽粮绝之时,我就厚着脸皮找个地方“卖”自己刚刚撰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所谓“诗歌”。初见刘小琴那次,我已经整整两天滴米未进了。为了活命,我从租屋斑驳的墙壁上摘下了两张明星图片,然后用飘逸的字体把自己最近两天写的几首有关人生感悟的小诗抄写在那两张明星图片的背面。我壮着胆子走上了街头——选了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巷,把那两张写满小诗的图片摊放在地上,并把自己最近几个月收到的一些样刊叠放在一旁。我的用意很明显,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路人的注意,并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同情。说白点,我这种所谓“卖诗”之举,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变相“乞讨”行为而已。
刘小琴是第三位驻足打量我的人。我清楚的记得她那天穿着一身紫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这是你写的诗吗?”她蹲下身子,指着明星图片上那些文字问我。我点着头,说,是的,这些诗是我最近两天写的。“那你一定读了很多书吧?”她偏着头问。我再次点了点头,说:“我读过大学”。她明显有些惊讶,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为了化解尴尬,我指了指图片旁边那叠杂志,告诉她,那些杂志都刊有我最近写的文章。她显得更惊愕了,连忙翻开那些杂志,问我的笔名是什么?哪些文章是我写的?最后问我这些杂志卖不卖?
到了这个时候,饥囊咕噜作响的我只好豁出去。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说:“这些书都是样刊,我自己想留着。我想卖的是写在图片上的这几首诗……”
刘小琴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掏出50元递给我。
“那我就买走你这几首诗吧!要是你愿意,我还是想拿本书……”她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杂志,轻轻地扬了扬。
既然她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怎么还好意思说“不行”呢?
我正欲对她说点什么感激之类的话,可她已经迈着轻盈的步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五
我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天后,我竟然在一种特别尴尬的场面下接连几次见到了刘小琴。
在那条小巷“卖诗”偶遇刘小琴之后的第五天,堂弟阿波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正躲在那间小租屋里写文章的我。在独自为我的落魄程度惋叹半天之后,阿波执意要我停下手中的笔,然后硬是把我拽出屋子,说是要请我去他们工厂门口的一家湘菜馆去好好喝几杯。那家湘菜馆与我住的小阁楼只隔三条小巷。我这才知道,阿波打工的厂子离我的租房其实也就四五百米远而已。
我和阿波刚在那家湘菜馆的一个角落里坐定,一阵熟悉的女声从大门方向传来。我循声望去,只见几天前曾掏50元钱向我“买诗”的那个漂亮女孩刘小琴,正挽着一个七十多岁的本地老头的手臂推门走了进来。直到他们在我们的隔壁桌坐定之后,刘小琴才猛然发现了我。在目光相撞的那一瞬间,我们彼此都从对方的神色里读出了惊讶。尽管我和刘小琴都极力掩饰着,装出一副彼此互相不认识的淡然模样,但待吴小琴和那本地老头走了之后,堂弟阿波就用力推了推我,说,老哥,你莫非看上刚才在隔壁桌吃饭那漂亮女孩了?
我没有直接回答阿波,而是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
“哥,你别装了,看得出,你对这个靓妹感兴趣。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孩我见过很多次,对她的情况略有了解,只不过她不认识我而已。”阿波一边说,一边举起了酒杯。
“你对她略有了解?那你说说刚才跟她在一起的那个老头是她什么人?”我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那老头就是前面飞西村本地人。小温已在他家租住了快两年了,跟那女孩比较熟。那靓妹据说是贵州人。你这么聪明的人,肯定早就猜出了她跟那老头的关系了吧?”说到这里,阿波脸上多了一丝坏坏的笑。
小温是阿波的女友,我见过几次。为了印证阿波的话,我后来还特意找小温打探过刘小琴与那本地老头之间的事。我从阿波女友小温那里的得到的信息是:刘小琴是贵州人,高中毕业刚毕业就来到深圳打工。因为喜欢唱歌,她最初曾在某歌舞厅打工了大半年时间。后来经人牵线,谋到了现在这份专职“照顾”那本地老头的工作。表面上,刘小琴只是帮那老头做做饭,洗洗衣,照顾一下他的起居。可实际上,刘小琴得满足那老头的所有需求。末了,小温还不忘戏谑般地调侃我几句。她说,哥,你们写文章的人总是这么多情,一个陌生的漂亮女孩也能让你们魂不守舍好一阵……莫非,你真的对她有了感觉?
六
我是一个对任何漂亮女人都会产生感觉的人。因此,对像刘小琴这样的女孩产生莫名的感觉,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不久之后,我竟然在某个特殊的场所再次尴尬地见到了刘小琴。
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堂弟阿波把我躲在横岭塘那间租屋码小说的消息透露出去之后,伙伴毅仁特意从广州跑过来看我。与毅仁在一起,最惬意的事情是你一杯我一杯地纵情喝酒。酒至二醺之态,毅仁提议带我去某个地方体验体验生活。尽管我一开始就猜出了他的意思,尽管我素来对去做此类龌龊之事有着强烈的抵触和反感情绪,但我那天竟然鬼使神差地跟在毅仁身后走进了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直到被毅仁推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狭窄的小房间,我才意识到了某些不妥。我正欲转身离去,随着“哐啷”的一阵关门声响,一个妖娆的女人身影挡在了我的身前。“先生,你躺下吧,我先替你按摩按摩!”一阵似曾熟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我抬眼一看,眼前这个已有半只胳膊抵在了我胸脯上的女人分明就是那个这几天一直莫名其妙占据我整个心空的贵州女孩。
“你,怎……怎么会是你?”我吐着酒气,涨红着脸问。
“是你?”那女人在认出我之后,也瞬间惊呆了。她条件反射般地松开抵住我胸脯的手臂,身子往后仰,用愕然的表情盯着我:“你一个读书人,怎么也来这样的地方?”
听了她的话,我哭笑不得。按理说,应该轮到我问你她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才对。可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尴尬身份,我除了难堪地噘噘嘴,委实找不到任何足可以证明自身清白的话语。
见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滑稽样子,刘小琴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她甩了甩自己的秀发,优雅地一个转身,挨着我坐在了床沿上。
“哎,先生,还是言归正传吧。你朋友点了一个钟,在这一个钟的时间里,我得替你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刘小琴在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之后,说出了令我浑身都快起鸡皮疙瘩的“行话”。
“什么服务?”我明知故问。
“别装了,来这地方的人,还有不知道服务内容的?”刘小琴的脸上多了些漠然。
“那你就陪我聊聊天吧!”我搓搓手,浑身不自在。
刘小琴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为了打破尴尬,我只得无话找话,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还自作聪明地说一看她就不像自甘沉沦的女孩,怎么会做这事呢,一定遇到了什么困难了吧?
对我的问话,刘小琴显得有些抵触。她最先说,你难道是在查户口呀?后来又故作夸张地叹息几声。
我赶紧说,你不愿告诉我也没有关系。我真的就只想跟你随便聊聊。
刘小琴这才抿嘴笑了起来。说,在这样的场合,哪有顾客问人家这么敏感的话题呀?末了,她说:“我说我叫刘小琴,老家在贵州,你相信吗?”
我当然只能是半信半疑。特别是她连续几次解释说,她之所以豁出去做了在常人眼里不可理喻的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去实现她想做一名歌手的梦想。
那晚,聊着聊着,我和刘小琴彼此都似乎有了找到知音的感觉。她后来甚至还鼓励我好好写作。还说如果有可能,可以把她当作原型写进我的小说里,不过前提是,不能把她写得太坏,写好后必须先拿给她看。
当伙伴毅仁来敲门提醒我已经到钟时,我和刘小琴聊得正欢。在开门离开之前,刘小琴突然一把抱住我,并在我脸颊轻轻地吻了两下。
“你是个好男人,以后要多多保重!”在推开我之前,刘小琴用甜美得不能再甜美的声音附在我耳根说。
我点了点头,然后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有下次,我一定会……”
我话还没有说完,刘小琴用纤细的手掌轻轻地堵住了我的嘴巴。
令人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在发生了一场始料不及的难以言叙的尴尬事之后,刘小琴像突然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似的,消失得无踪无影。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过她的任何消息。
但不知何故,这些年,不管我身处何地,不管经历了何种际遇,几乎每时每刻,我的脑海里都会不经意地浮现出刘小琴妖娆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我曾一度把刘小琴幻化成了“女神”般的存在——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一种莫名的愧疚与自责情绪的影响下,我对她的自甘沉沦的那段经历有过种种极其矛盾的复杂情愫。
七
我万万没有想得,在时隔二十年后,我竟然能够遇见刘欣这样一位与刘小琴不管是外形还是神韵都几乎完全一致的人。更没有想到,还阴差阳错地和她成为微信好友。最为关键的是,在有意无意地几次试探性的瞎扯之后,这位酷似刘小琴的名为刘欣的当红女歌手还渐渐对我产生了兴趣。
这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效果,源于我这些天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只要一有空闲,我总要不厌其烦地做同一件事: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刘欣的原创歌曲,一边厚着脸皮给她发暧昧得不能再暧昧的话语。
刘欣是在我第三次发出“我很喜欢,一边想象着你的倩影,一边听你的歌,一边任思绪信马由缰的感觉……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多年来苦苦等候的那个人……”这样戏谑般的直裸“告白”之后,才回复了我一句令我更加浮想翩翩的话:“你这人说话真有趣,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一看就是个情场老手,莫非你真的想打我的主意?”
对付女人,我最擅长的就是把捏好与她们交往的“度”。换句话说,就是懂得如何把“欲擒故纵”的伎俩用到极致。
我并没有直接回复刘欣“莫非你真的想打我的主意?”这个问题。而是在发给她一个“偷笑”的图标之后,把自己最近完成的那篇万字小说《谁是奥斯卡》转发给了她。
老实说,我的那篇万字小说《谁是奥斯卡》是写给自己想象中的所谓梦中情人的。在我杜撰的那则算不上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里,无数个似曾熟悉却又陌生的女人像幽灵一样出没在男主人公原本就混乱不堪的生活圈里。无一例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带着面具生活。他们用最拙劣的手法在自欺欺人。可悲的是,在一个被无数虚假暗影充斥的空间里生活得太久了,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最初的某个小小的贪念,一不留神就成了一切悲剧的根源。
我不知道刘欣是否看完了我的这篇万字小说。但显而易见,我的这一招起了效果。第二天一大早,刘欣破天荒主动给我发来了“大才子,早安”这样的问候语。末了,她还补充了一句:“跟你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若方便,很想当面向你请教一些写作方面的问题。”
我们把见面的地点约在了“前世缘”咖啡店。为了制造一点神秘气氛,我那天特意戴了一副深色墨镜。
刘欣则穿了一浅蓝色连衣裙,显得干净纯洁而有女人味。
“您就是蒲扇先生吧?”刘欣站在我面前,眸子里闪着摄人的光亮。
“久仰,美才女!”我示意她坐下,然后轻轻地摘下了眼镜。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见你吗?”刘欣眨巴着眼睛,眸子里依然闪着冷峻的光亮。
我没有想到她开口就问这样无从回答的问题。
我摇摇头。只好无厘头地回复了一句:“这怎么说呢!”
刘欣依然没有一丝特别的表情。她用冷峻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我,然后问:“你难道不觉得我们之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吗?我们此前是不是曾见过面?”
刘欣的这句问话,是我预料之中的事。
我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为了缓解尴尬,在微微一笑之后,我调侃道:“很多人都说我长着一副大众情人的相貌,莫非我们曾在梦里见过?”说完,我摆出一副与女人周旋时惯用的——标志性的“嬉皮赖脸”。
刘欣并没有因我的调侃而放松警惕。她依然一脸戒备地不停打量着我,眉头似乎越皱越紧。
“蒲扇先生,非常抱歉,我有点急事,失陪了。”她忽地站起身来,优雅地同我挥挥手,然后扭头转身匆匆离去。
即使再笨拙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
我心中有了确切的答案。直觉告诉我,这个刘欣分明就是我当年所认识的那个刘小琴。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刘欣似乎也认出了我。只是,她的匆匆离去,是一种本能不过的条件反射?还是另有其因?
我设想过刘欣认出本人就是当年那个流浪诗人冬天之后的种种反应,就是没有想过她竟然会在第一时间拉黑我,并且还在拉黑我之前对我下了最恶毒的诅咒。
她在离开那家“前世缘”咖啡厅不到十分钟就给我发来了信息。信息里只有一句话:居心不良的人最终都会遭报应。
我并非居心不良的人。想办法接近刘欣,完全出于一个小说写作者对过往生活的惦念及对原真生活的好奇。我也并不想打扰她现在的生活。对她,我只不过出于一种发至善意的关注。当然,这也与我内心那种期待得到认可的虚荣心态多少有点关系。换一种说话,我还有想要让已完成华丽转身的刘欣知晓——当年与她在坪山偶遇过几回的那个落魄至极的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生了人生的蜕变。
不过,还有一点是我自己永远不愿承认的。作为一个天生就痴迷于漂亮女人的不羁男人,我内心的那份不言自明的期待,与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的征服欲才是主动去接近刘欣的真正原因。
理所当然,得知刘欣已把我拉黑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嘲式的苦笑几声。
八
从那家“前世缘”咖啡店出来,我随手招了计程车。刚坐进车里,我的手机嘟嘟响起了提示音。打开一看,是一个网名为“昨天”的陌生人发来的添加微信好友的请求。
我素来没有添加陌生人的习惯,但仔细看了一眼对方请求添加好友的理由之后,我有了某种莫名的心悸之感。
“一个能给你指点迷津的人。”多么狂妄自大的话语!我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对方添加好友的请求。但几乎同时,极度敏感的我也本能地把这人与不久前刚刚拉黑了我的刘欣联系到了一起。
“先生,你要上哪?”一阵轻柔的女声从前排驾驶室传来。我这才想起自己只顾看手机,竟然忘了乘坐计程车必须完成的第一道程序——告知司机本次乘车的目的地。
“四角楼。”我随口回答。但也就在我话音未落之时,那一身红装的女司机回头朝我瞥了一眼,四目对视的瞬间,我愣住了:这个红衣女子竟然与我刚刚约见的刘欣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年轻十来岁的样子。她显然不可能是刘欣本人。那她是谁呢?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遇到这么神似的两个人?
“靓女,你贵姓?”我问。
我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波动,想通过这样平常的问话从侧面了解一点什么。
“免贵姓刘,你叫我阿芳好了,大家都这么叫我。”红衣女子回头冲我浅浅一笑,然后启动车子一路向前。
姓刘?难道???我不自觉地多了些想法。
“听你口音是湖南人吧?”我进一步试探性地问。红衣女子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了句,“我才说了几句话你就能够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我是哪里人,看来你的见识真广!”
我决定不再兜圈子。于是我问,听说我们莞城有个名叫刘欣的女歌手,最近很火,她该不会是你什么人吧?
“刘欣?没听说过。”红衣女子摇摇头,接着说,我一个普通女孩,怎么可能跟别人女歌手扯上什么关系呢!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在红衣女子面前谈及刘欣的话题了。但敏锐的第六感官告诉我,似乎还会有我意想不到的某些事儿发生。
车子才往四角楼方向开出不到一公里,就遇到了堵塞。“要不,我们从山子村附近那条小道走吧?”红衣女子指了指拥堵的车流,向我提议。我回答说,车子是你的,你想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吧,你只要负责把我送到四角楼就行。
听我这么说,那红衣女子回头冲我妩媚一笑。于是她挤出车海,把车子开上了公路右侧的那条铺满卵石的村道。
正在这时,那个自诩为能给人指点迷津的——名为“昨天”的人给我发来了信息。那条信息只有与令人浮想翩翩的五个字:猜猜我是谁?
这绝对不是在玩什么孩童游戏。我敢肯定,对方如此发问,一定是有所指。那对方究竟是想暗示我点什么?难道是在暗示我对方与刘欣有关联?
在稍稍踌躇之后,我回复道:“那你先猜猜我是谁?”
“我说冬天先生,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要不知道你是谁,我还会加你的微信吗?”对方很快就回复了我,而且还直截了当称呼我为冬天先生。
尽管有思想准备,我还是惊讶到了极点。原因很简单,“冬天”是我二十多年前用过的一个笔名,现在还能把“冬天”这个笔名与我联系在一起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我的笔名,她只可能是一个人——刘小琴。
“你是刘小琴?”我用最快的速度敲出了这几个字。在点击“发送”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还未等对方回答,我又立马发送了另外一句——“如果我猜得没有错,你就是刘小琴,不,你就是刘欣!”
除了一个夸张的“大哭”图标,“昨天”并没有直接回复我。尽管接下里我又发送了几条类似的信息给她,但都没有收到回复。
我很纳闷,猜不透“昨天” 究竟在玩什么花招。
我只顾低头给“昨天”发信息,竟然连计程车跑偏了方向也没有发觉。直到随着“嘎”的一声,小车停在了一个极其偏僻的陌生小院里,我才意识到了不妥。
“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带我来这里?”我伸手拽了拽正在拉手刹的那个自称“阿芳”的红衣女子的衣袖,充满警惕地问。
“不好意思,我是受人委托,才把你载到这里来的。”红衣女子一脸的淡定自若。
受人之托?一切都太突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一股莫名的恐惧悄悄挤占了我的脑海。
“快带我离开,我现在只想回家,不愿见任何人。”我一把抓住正在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的红衣女子的右手手腕。红衣女子没有挣扎,也没有出声,而是偏着头用诡异的眼神看了看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不说话?快点带我离开这里!”我压低了嗓子,用发颤的声音冲那红衣女子说。
红衣女子依然没有出声。只是用手指了指车窗外边。
我赶紧转过头,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车窗两旁不知何时分别站着一个身穿素衣的健壮男子。
“他,他们是谁?”我松开那红衣女子的手腕,脸上全是惊恐。
红衣女子轻轻地甩了甩那只被我拽过的手腕,没有回答我。
九
我记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被人拽下车的。
直到我被人连推带拖来到了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我才被一阵悦耳的歌声从混沌中惊醒过来。
“你还认识我吧?”在那悦耳的歌声戛然而止之后,一阵沙哑的女声传进了我的耳膜。我猛地坐直身子,这才发现四五步之外的一架半新半旧的钢琴旁,一位与刘欣长得神似的黑衣女子端坐在一把老式藤椅上,正用一双深邃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我。
“你,你才是刘小琴!”我脱口而出。但随即,我又自相矛盾地连连否认:“不,你不是刘小琴。”
“哈哈,我是不是刘小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记得刘小琴。”黑衣女子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站起身来。她那亭亭玉立的高挑身段和说话时那悠雅的姿态俨然与二十年前我在飞西村街头遇到的那个刘小琴一模一样。
“你和刘欣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想见刘欣,你们快带我去见刘欣!”到了这个时候,再愚钝的人,也能猜出个大概——这一切之一切,都应该与刘欣有关。
“作家先生,你的联想能力还挺不错嘛!”就在这时,随着“咯吱”一声,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墙壁上,一道暗门忽地被打开了,一身浅蓝色连衣裙的刘欣依靠在门框上,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问:“你想见我,是为了逃避,还是心虚?”
果然如我所料。在轻轻瞥了一眼刘欣之后,我避开了她的目光。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刘欣。
奇怪的是,我不说话,刘欣和面前那黑衣女子也默不作声。她俩不时交换着眼色,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我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短暂的慌乱之后,我渐渐理清了头绪。理智告诉我,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应该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许多。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弄很清楚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真正用意。
于是,我用相当委屈的口吻打破了沉默:“我说大歌星,我不过就因为欣赏你才斗胆加了你的微信,在微信里跟你调侃几句,进而邀约你见了个面嘛?我对你并无坏心呀?你们这样做难道是认为我在哪个方面冒犯到了你们吗?”
我这话是对刘欣说的。两个女人静静地听着,她们除了偶尔彼此使使眼色,并没有人搭理我。
我明白她们的意思。她们是嫌我还没有把问题讲到关键点上。
“哎,还有一点我得承认,在最初见到美女歌手的那一刻,我把你当作了我当年在深圳接头偶遇过的那个美丽女孩。对了,我想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黑衣美女,你是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刘小琴?”说到这里,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个一直静坐在钢琴旁的黑衣女子。
那黑衣女子只微微地眨了下眼皮,然后,她与我身旁的刘欣对视了一下目光。她依然没有回答我。
“我说蒲扇先生,亏你还是个写文章的人,你是在故意装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把你找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呢?”说这话的是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刘欣。
“什么原因?不就是刚才在咖啡厅与你一言不合,你就不辞而别,然后你就拉黑了我吗?我一直很纳闷,一直弄不明白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冒犯到了你!”我一边反问,一边解释。不过,我刻意回避了当时在咖啡厅自己曾一度把刘欣误认为当年的吴小琴那一微妙心理。
“哈哈,我说大作家,你果然是在装糊涂。我问你,你约我在咖啡店里见面,是不是想证实我是不是就是当年曾遭过你们黑手的刘小琴?”刘欣加重了语气。我明显感觉得到,她眉宇间那股冷森森的杀气。
“遭黑手?”我甚为诧异。“你是说她遭过黑手?”我本能从椅子上蹦跳起来,用手指向那黑衣女子。
在与黑衣女子目光相碰的瞬间,她那眸子里射出的寒光令人不栗而颤。
我的心里猛地一惊。
刘欣上前两步,按住我的肩头,示意我坐下。
我无力地埋下头,不敢抬头正眼看她们。顿时,心里最隐秘的一段往事瞬时重新交织在我的脑海里。
我清楚记得那是伙伴毅仁带我去那个特殊场合而“偶遇”刘小琴之后的第八天。堂弟阿波邀我去他女朋友小温位于飞西村新联路的租屋吃饭。我欣喜赴约,原因很简单,小温租屋的房东就是我所认识的美女刘小琴当时在“照顾”的那个本地老头。
待我赶到小温的租屋,才发现屋里除了堂弟阿波及其女友小温之外,还有国弟、歪嘴、猫皮子三位在我们老家米坝出了名的混混,以及另外两位我并不认识,但一看就不是正经人的陌生男子。待酒过三逻之后,国弟直接说出了他们几位混混齐聚小温租屋的真正原因——几天前,他们从我伙伴毅仁嘴里打听到阿波女友小温的房东“包养”了一个来自贵州的漂亮小妞,因此,他们约伴过来找机会“饱饱眼福”。
那是我这辈子最愧疚的一段经历。当国弟几人借着酒气怂恿阿波女友小温去察看那个本地老头是否在家时,我竟然没有出面阻止。特别是当小温回来告知国弟他们,那本地老头有事外出了,只剩刘小琴一个人在二楼的客厅里练歌这消息后,国弟几人壮着酒胆说是要去见识见识刘小琴时,我不仅不敢出面劝阻,反而找个借口提前开溜了。
喜欢逃避,是我性格中最大的劣根性。那之后,我从未主动向堂弟阿波打听过国弟等人当天的所作所为。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国弟几人那天所做的龌龊事很快就在老乡当中传开了:国弟几个混混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在骗刘小琴打开了房门之后,竟然趁着酒气,不顾刘小琴反抗,轮番欺凌了她。最令人不齿的时,当他们的恶行被中途赶回家的那个本地老头撞见了之后,他们竟然把那老头子拖进客厅一顿暴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事儿一直被国弟几个混混当作炫耀的资本四下吹嘘。而我更是不经意间从已经与堂弟阿波分了手的小温那里了解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据说,在离开之前,国弟几人威逼刘小琴唱几句下流的山歌来助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刘小琴硬是倔强地紧闭嘴巴一字不哼。羞恼成怒的国弟几人竟然做出了丧尽天良之举——他们竟然撬开刘小琴的嘴巴,把一大罐辣椒水灌进了她的喉咙里……
十
尽管我一遍又一遍跟眼前的两个女人解释,我并没有参与当年那场恶行。但从她们冷漠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她们并没有相信我的解释。
在那黑衣女子轻轻地几声哀叹之后,两个女人一声不吭推门离开了。我起身追了过去,却被之前见过的那两个壮汉挡在了屋内。随着“哐啷”一声,一把大锁锁住了大门。
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被关了整整两天。
在那漫长的两天时间里,除了窗外偶尔有一两个似曾熟悉的人影在晃动,整个世界离奇的寂静。
就在我饥渴难耐,自认为身子已经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房门“咯吱”一声被打开了。我定眼一看,站在房门外的人竟然是城区作协的“郭大侠”。
“我是来接你的,你先喝几口水。这是你的手机。什么话都先别说,这事儿我们以后慢慢捋。”郭大侠在递给我手机的同时,把一瓶已拧开了盖的矿泉水凑到我嘴唇边。
郭大侠并没有直接把我送回家。他把我带到路边的一家小吃店吃了碗米粉,然后开车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赶。
“郭主席,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我终于忍不住发问。
“你去了就知道了。”郭大侠说。我和郭大侠仅仅只是认识而已,算不上很熟,况且他是有职务的人,我与他原本就有某种隔阂。因此,既然他都这么说,我也就不便多问。
小车左转右拐,大约二十来分钟之后,郭大侠把车停在了一个小山坳上。
我跟着他下了车。穿过一片灌木林,一块石碑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
“你走进看看就明白了。”郭大侠示意我。我心怀忐忑地走向前去。石碑上的字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刘小琴之墓”几个字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
“这怎么可能?难道两天前我见到的那个黑衣女子不是刘小琴?”我连连后退,直到郭大侠拽住了我的衣角,我才停了下来。
郭大侠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见我依然一脸疑惑,他才说:“我也是受人所托才带你来这里的,具体内情我也不太清楚。你还是打开微信看看吧,或许微信上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我打开微信,果然有几条还未查看的信息。信息都是那个名为“昨天”的人发来的。第一条信息是:“冬天先生,我托人带你去的那个地方你去了没有?”第二条信息是:“你要找的刘小琴已死。”第三条信息是:“刘小琴的死你是有责任的。可你这些年却安然地活着,这公平吗?”最后一条信息是:“那间黑屋子曾是刘小琴生前长期住过的地方。原本想要把你长久地关闭在那屋子里,然后让你替刘小琴陪葬,只是……”
看着这些文字,我除了惊恐还是惊恐。
我感觉自己的整个脑袋都嗡嗡作响,似乎都快爆炸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我回复道:“你到底是谁?是刘欣?还是那位黑衣女子?你和刘小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怎么可能是刘欣?你身旁的郭大侠没有告诉你吗?刘欣现在早已经在飞往澳洲的航班上了。”那个名为“昨天”的人也飞快回复了我。
“这么说,那你就是我见过的那个黑衣女子了?”我顺着对方的话问。
遗憾的是,不管我怎么问,对方都再也没有回音。
十一
回到四角楼我上班的单位,才知道这几天大家都在为我的突然“失踪”而焦急不已。单位领导关心地询问我这几天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还含蓄地征求我的意见,意思是要不要考虑报警。
我委婉地谢绝了领导们的好意。不过,我借机跟领导请了一周的假。
我心中还有太多的谜团需要时间去慢慢解开。比如,郭大侠到底是受谁所托,把我带到那个立有“刘小琴之墓”的荒野?坟墓里的那个刘小琴是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刘小琴?如果不是,他们把我带到那块墓地上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如果是,她一个贵州女孩怎么会安息在那个地方?再则,如果坟墓里躺着的真的是刘小琴,那个名为“昨天”的人又怎么会知晓我就是当年在深圳街头偶遇过刘小琴的“冬天”先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刘欣在整个故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个黑衣女子究竟与刘小琴有什么关系?还有那长相与刘欣神似的——把我带到那座偏僻小院的红衣计程车女司机,以及一直把守在那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门口的那两个健壮的男人,又分别是什么身份?最最关键的是,他们当初明显有要置我于死地之意,为何又突然良心发现,通过郭大侠重新给了我生机?
我隐隐觉得一道道暗影在我原本就杂乱不堪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
我决意独自再到郭大侠曾带我去过的荒野里走一走。我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那块刻有“刘小琴之墓”字样的墓碑找到解开心中谜团的蛛丝马迹,进而证实的自己某种大胆猜测……
只是,在暗影恣肆的时空里,我能如愿以偿吗?
-

- 探秘地底不为人知的秘密,有多少是你所忽视的(2)
-
2024-04-27 05:04:50
-

- 「名著导读」《西游记》知识点都在这里了!
-
2024-04-27 05:02:47
-

- 中国大案要案纪实|石城枪声(石城县1994年命案)
-
2024-04-27 05:00:43
-

- 那些校园传言果然是真的,我才来学校两天就两次在宿舍遇到鬼
-
2024-04-27 04:58:39
-

- 短篇小说《阴影》
-
2024-04-27 04:56:36
-

- 10块钱买的琥珀,一百块卖掉,赚了九倍(10块钱买的琥珀,一百块卖掉,赚了九倍
-
2024-04-27 04:54:32
-

- 五人出游三人藏尸冰柜案背后:邪教全能神组织洗脑全揭秘
-
2024-04-27 04:52:28
-

- 三人藏尸冰柜案背后:死者生前曾入邪教 洗脑过程揭秘
-
2024-04-27 04:50:25
-

- 故事:教学楼5楼密封了20年,有人误闯后,学校开始怪事连连
-
2024-04-27 04:48:21
-

- 公交车上遇见个女孩,以为桃花运,结果...(胆小慎入)1
-
2024-04-27 04:46:18
-

- 故事初恋失败我不相信爱情,和大八岁男神相处3月,却再次动心(知乎上很火的
-
2024-04-27 04:44:14
-

- 全本八扇屏文本
-
2024-04-27 04:42:10
-

- 三分钟小故事(三分钟小故事幼儿)
-
2024-04-27 04:40:07
-

- 杨过爱的一直都是郭芙(杨过为什么爱郭芙)
-
2024-04-27 04:38:03
-

- 每日鬼故事-荒村鬼影(荒村鬼事一个人一个鬼故事)
-
2024-04-27 04:36:00
-

- 16个民间灵异故事集,高速冤魂、冥婚……相信我,你们会喜欢的
-
2024-04-27 04:33:56
-

- 民间真实老故事(民间真实老故事300字)
-
2024-04-27 04:31:53
-

- 汉瑶乡儿童失踪事件(小说)
-
2024-04-27 04:29:49
-

- 我八岁被娘卖给病夫做童养媳,后来我被倒手卖了三回。
-
2024-04-27 04:27:45
-

-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50篇(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
2024-04-27 04:2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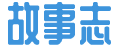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赛罗奥特曼睡前故事30篇
赛罗奥特曼睡前故事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