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阴影》
短篇小说《阴影》

王军强
一
你们不知道或者说看不出来,我有心里阴影,它就像恶魔随时发飙。我曾试图去医院看过心理医生,在众多心理求助者中他们会不会都像我这样?他们看我的眼神儿并非异样,有的还露出善意微笑,那微笑我完全能够读懂和理解,面对陌生人有时我也会露出这样的微笑,我对这样的微笑非常珍惜,这种心情无人可以理解,有一个看上去跟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一直在微笑看我,路过他身边他还冲我善意地点点头,看来他和我一样也是来看心里医生的,他在我前面走进六号诊室,我坐在他腾出来的座位上静静等待着。大夫说我是中度患者,他跟我的判断差不多,我觉得我早已过了轻度症再不看医生我就会成为重度患者,它让我惧怕。他坐在对面桌子上,手里把玩着一支红色圆珠笔,红色圆珠笔在他手里翻上翻下像一个手彩儿魔术师,他慢慢停下手里笔表情认真看着我。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年华,大夫问了我很多事情,包罗万象,问我交没交女朋友对爱情怎样看,我知道交女朋友意味着结婚,这是我最恐怖最害怕的事情。他问的最多是我儿时到少年事情,那段时光所有事情是我记忆中最深刻最清晰最难以忘掉的,它们历历在目。他让我别紧张慢慢放松肌肉,想起什么说什么,一个一个来。那会儿我把他当成最亲近人,我说有些事情一直装在我心里,可能是我第一次说出来,不知为什么我却愿意讲给你听。他不说话,微笑着看着我,他的微笑让我心里非常舒服,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我渐渐安静了下来,情绪也变得平静了许多,我说那我就跟您讲吧。他把眼镜轻轻往上推了推,靠在椅背上说,可以,讲吧。
我先想到的是父亲,他念过初中,在他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我记得我上小学时他还能辅导我写字做数学题,他喜欢写毛笔字,总想培养我,教我写他说是欧体的字,我对写字一窍不通,一点兴趣没有,写过几次他就不教了,说我不是那块料不可雕琢,嘱咐我学好数理化就行。母亲只念过小学,她说学不学习其实没什么用处,到时托人找个工厂上班就是了,她把上班看的比学习还重要。他们的婚姻是我姥爷和我爷爷撮合的,生我之前我无法知道他们婚姻是否美满,等有了我到我记事才知道他们的婚姻并不如意。母亲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发火骂街,一件不如意小事或一句不受听话,都会大动干戈,让它不断发酵。父亲最初没有脾气,后来变了,起初他不搭理母亲,嘚嘚烦了,就会像一包火药突然燃爆发,这场面并不能镇住母亲,反让她斗志更加旺盛,那阵势定要压过父亲,他们谁也不服,在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下又一场战斗瞬间爆发。
先是母亲动用武器,手里拿着鸡毛掸子,上面的鸡毛几乎所剩无几,这个鸡毛掸子对父亲没有任何威胁,母亲刚要打过去,腕部便被父亲一手抓住,母亲不死心用头狠撞父亲胸口,撞了几下,父亲就不再容忍,愤怒地抓住母亲头发向后一推,母亲就没有了反抗力。肢体被制住但嘴却自由,母亲破口大骂,每一次都是这样,把父亲骂得分文不值,什么狠骂什么,战斗很快结束,父亲手上挂了彩,母亲也没幸运,手腕疼了好几天。有好些日子他们谁也不搭理谁,在饭桌上各自吃各自的,我不敢多说话,多说话就会被莫名其妙训斥,气氛沉闷又压抑。到了外面情况便不一样,他们对街坊邻居非常好,父亲和蔼可亲谦恭客气,母亲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从没跟邻居红过脸,在邻居眼里他们是让大家羡慕的,是一对性格和睦脾气很好的夫妻,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父母的真实一面。
他们每次打架都是我心里最灰暗的日子,那种毫无顾忌声嘶力竭的吵骂场面,时刻浮现在我眼前,我分分钟也不想呆在家里,怕看到他们的战斗。有一次天晚上他们又开战了,打到最凶时候我受不了,一个人跑了出去,我站在栋口茫然不知所措,想不起来要去哪要到什么地方,那会儿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楼下空无一人,西北风刮着干树枝和电线发出凄厉的怪叫,他们全然不知我的消失继续他们的战斗,我从楼下隐约能够听到屋里摔东西声音,那声音非常耳熟,是战斗到最激烈时候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家里印有小红花的那些玻璃水杯已经所剩无几,都是母亲战果,父亲不会有这种杰作,在我记忆中父亲只会发发脾气骂骂街,最多用手抓住母亲做一做恐吓动作,那动作也只是做做而已,并无实质效果和作用。
我有一次看不下去,背着母亲问他,我说我妈每次跟你动手你怎么不还手呢?是不敢还是天生就怕我妈?他说你认为我怕你妈吗?我是怕他吗?我要是动手弄不好能把她打坏了你信不信?所以,我不动手不是我怕她,一个瘦小经不住三拳两脚的女人我有什么可怕的?你爸我年轻时在外面怕过谁?你妈知道,男人不要在家称雄称霸尤其是跟自己女人,那不叫本事,外人知道会笑话,我不跟你妈动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说那也要有个度差不多,每次看你们打架我觉得你狠怂。他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事情不懂。那会儿我十来岁对他的做法的确有点不懂。
那天夜里我身上分文没有,一个人在龙泉澡堂大厅椅子上睡了一宿,那一宿我睡得迷迷糊糊一点也不踏实,从头到尾都伴随着噩梦,母亲用刀亲手把父亲砍死了,献血顺着父亲脖子突突往外流,母亲怒目圆睁,似乎还不甘心罢手又举起手里菜刀朝父亲不停砍去,父亲终于被母亲手里的菜刀砍倒在地,在痛苦中父亲倒在地上慢慢失去知觉,血流一地,殷红一片……我被收留我的那个夜班大叔推醒时候满脸泪水,我能感到我的心还在惊吓中慌乱而又急促跳动着。他弯下腰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做噩梦了吧小伙子?我坐起来揉着还在流泪的眼睛,突然悲伤起来,我说我爸被我妈用菜刀砍死了。
大叔说不会的小伙子,是你做的一个梦。
我说我知道叔叔,可是我害怕,我怕我妈有一天真的把我爸砍死了。
不可能的,他们是两口子怎么会呢?
我说他们总打架,我妈特别凶,我爸怂。
大叔笑起来。他的笑让我心灵得到了安慰,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梦不会发生在生活中,母亲也不会干出那种事请,那场噩梦始终让我无法忘掉,它就像一个幽灵时刻伴随着我。父亲跟母亲都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后悔,父亲说我不怪你,以后不要再跑出去了好不好。我不说话。母亲也诚恳地说,都怨我和你爸,我们以后保证不再打了。我说你们能做到吗?母亲说能做到,你放心吧。父亲也说我和你妈保证不再打了。他们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竭力让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改掉的。我真心希望能是真的,但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改掉却义无返顾继续着。
二
有好几次他们就要爆发的战争都被我惊恐的眼神儿屏蔽了,我看到他们都在努力压抑控制着自己情绪,父亲坐在凳子上看着窗外,胸脯一起一伏,里面蓄满了随时可燃的火药;母亲虽然一句话不说,目光里却充斥着愤怒和不可侵犯。我知道是我的原因导致他们无法发泄,他们无可奈何又不得不面对,我想马上离开这个屋子,不想看到那种场面,它让我感到害怕恐惧。父亲似乎看出我的想法,问我干什么去。我看出他眼里流露出不想让我走的意思,他分明是不想跟母亲再战了,他的目光让我犹豫了,他可能和我一样恐惧了那样的场面,我说我去厕所。他的表情瞬间变化了不再显得那么紧张。
我反锁厕所门一个人在里面呆了很久,两家共用的一个厕所,卫生自然不如人意,纸篓里堆满了两家人用过的大便纸以及对门女人刚刚用过的卫生巾,空气里弥漫着恶臭味儿,我嗅觉不那么灵敏都在第一时间闻到了,恶臭味儿让人很不舒服甚至有些作呕,但这里却让我感到非常安全和踏实,我透过厕所上面的小窗户看着外面的柳树枝,四月的早春虽然凉意还在袭扰着肌肤,但春意渐浓,柳枝上已经悄悄钻出树芽,淡淡的绿色,嫩嫩的,有一枝就在我们阳台前,它好像有意朝我伸展过来,我能清晰看到上面的柳树芽,我用眼一个一个仔细数着,如果没数错的话,一共有三十六个小嫩芽,每一个嫩芽都像是一个小小的蓓蕾,有的已经从里面长出许多小绿叶,绿叶有的大有的小,形状各异,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就像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最长最大的应该是父亲,小它一节的应该是母亲,而下面那些小小的嫩嫩的一定都是它们的孩子,孩子们紧紧拥抱着他们的父母,好像在仔细倾听父母聊天,又好像仰脸在认真跟父母说话,它们一定也有语言也有思想只是我听不见看不到。我不知道在厕所里呆了多久,也不知道都想了一些什么,我听到有人敲门:完了吗?是父亲声音,他说他也要上厕所,声音跟之前判若两人,我能猜到他不是来上厕所,真正目是来看看我在没在厕所里,他真的是怕我走了。
我回到屋里,他很快也回来了。他对我说里面太味儿了,那个纸篓垃圾好多天没人去倒,我现在去把它倒掉。他的话实际上是说给母亲的,他是在找机会或者说是想主动跟母亲妥协。我把脸转向母亲,看着她,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就坡下把僵局缓和下来。母亲不说话,谁也不看,低头弄着手里针线活,那是父亲一个冬天穿过的秋衣,她在给父亲缝补上面的开缝。我去厕所那会儿她手里还什么都没有,秋衣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的?我能感觉到母亲之前也在默默向父亲示好。我对父亲说我去把它倒了。我这句话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母亲抬起头说你别去,就让他去倒!上一次是对门老孙倒的,这回该咱们倒了。
母亲声音带着极度不满,口气像命令。父亲很快接了下句,他说我去吧,你把地帮你妈妈扫了。母亲说不用已经扫过了还扫什么?话里还带着情绪。父亲不再说话,乖乖转身出去了。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快就缓和了下来,是因为我去厕所那会儿父亲举起免战牌了,还是母亲大仁大义放了父亲一马才让父亲侥幸躲过一劫?那些天我们家气氛格外好,父亲每天下班带回来都是阳光和微笑,母亲也不例外,回到家也是满面春风,我心情比他们还好,眼里的天都是蓝蓝的,阳光也是大方不吝啬的,我们家靠窗那张大床上,每天总是阳光一片,床上褥子枕头伸手摸一下都是温暖的,生活真好。我那些天食欲特别好,能吃能喝能睡,每天疯玩的满头大汗,邻居都说我变了一个人,我自己也能感觉到。
有一天我在楼下跟小伙伴们踢球,父亲下班看到后,搂着我的肩说,喜欢吗?我知道父亲指的是什么,我没说话,但心里非常希望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足球,我想张嘴找父亲要,又知道父亲没有财政大权,他平时所有支出都由母亲管控着,就是想给我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想为难他。几天后父亲给了我一个惊喜,那天回家床上放着一个崭新的足球,那迷人的黑白八角块让我受宠若惊,我惊讶在门口时候,父亲说,是你妈同意让我给你买的,还不谢谢你妈,他用眼神示意我。其实这已在我意料之中,那是我十三岁生日,父亲圆了我一个梦寐以求梦的梦。那天晚上母亲给父亲倒了一杯白酒自己也倒上一杯,还主动敬父亲,在我记忆中这样场面没有过,也许父亲太过感动,那天喝多了。母亲让他躺到床上时他向母亲提了一个要求,他要亲亲她。他可能忘记了还有一个第三者的存在,母亲没同意想用力把父亲从他怀里推出去,但母亲身单力薄没能推开父亲,父亲得寸进尺把母亲紧紧搂在怀里,这画面就像她们战斗时她被父亲死死控制时的那样,父亲用嘴努力寻找不停躲避的母亲,我不想看下去,逃出屋,这次我没有躲进厕所,一直跑到了楼下,楼下有好多小伙伴正在明亮的月光下玩耍。
我被母亲喊回家时,父亲已经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注意到母亲唇边有一个浅浅的唇印,那一定是父亲留下来的。夜里我听到有人说话,声音虽然被有意压低,我还是听见了,母亲似乎在问父亲是不是还跟以前那个女人有联系?父亲的意思说从来没有过。母亲好像不相信,说不可能,你和她搞过一年多对象不会一点感情都没有。父亲说以前有过现在一点也没有了,我已经娶了你不会再跟人家有感情的。母亲说你骗我,刚才你说梦话时我都听见了。父亲说我说什么梦话了?母亲说你自己知道。那一宿我几乎没怎么睡,我一直支棱着耳朵偷听他们说话,如果他们之间再次发生战争,我会在第一时间冲出屋门什么都不管。
三
听奶奶说父亲跟第一个女孩分手原因并不是他们没有感情,父亲很喜欢那个女孩,因为外公跟爷爷的想法和撮合,一对情人才无奈分道扬镳,一年多情感的种子已经在父亲心里种下了。我问奶奶为什么爷爷和外公要把他们拆散呢?奶奶说爷爷跟外公是老革命老战友,战场上外公对爷爷有过救命之恩,他们不知道爸爸那会儿已经背着他们处对象了,后来他们知道但为时已晚,父亲已经娶母亲成家。最初父亲舍不得,生死离别感觉让他难以放下,为这份爱情流下了许多泪水,可最后他还是做了一个孝顺儿子,跟女孩分手让他大病一场,好长时间才挺过来。那种感觉会有怎样的强烈我不知道,奶奶给我描绘过那个女孩,一位漂亮女孩在我心里悄悄驻下了,我偶尔把这个女孩和母亲做一对比,设想如果这个女孩换作是我的母亲,她会和父亲发生战争会有那么凶吗?现实不会有答案,但我总会在幻想中给出如我心愿的美好答案:美丽、善良、体贴、温柔、相夫孝子,女人的一切美好优点我都希望集她于一身。有一次我背着母亲悄悄问父亲,我说那个女孩是不是比我妈好你特别喜欢。他看着我凝望了好一会儿说,每个人是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我说你还是想念她对吧?那会儿我已经成年,父亲也拿我当成了大人。父亲说那个女孩是我的初恋,初恋对于任何男孩和女孩都是到死难忘的,你现在还不懂,等你有了初恋女孩你就体会到了。我说你可以不听我爷爷的,命运要自己掌握。父亲说年代不一样你理解不了。我说是为了对长辈的孝顺吗?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是吧。我说那就可以自己毁掉自己幸福?父亲脸上表情看上去有点悲伤,他用略带厚重的声音强调,我说过年代不一样你不懂。他不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我完全理解。
那一回是我们爷俩第一次平等交谈,真正的男人与男人对话是推心置腹的。有一天,可能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父亲下班进了屋突然跟母亲暴怒起来,这次他们完全没有顾忌我在一旁的感受,父亲脱掉上衣,沉着脸一句话不说,用力朝床上甩去,上衣从我头上悬空落在床上,看着落在床上那件上衣,我蒙掉了,他吃了豹子胆还是脑子进水了?他在向母亲发起挑衅?我下意识看着父亲,他脸色铁青,无任何表情,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怎么了?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有些紧张,我把目光投向母亲。好像父亲的状态并没有把母亲吓住,她面无恐惧平静而自然地坐在床边,发现我在看她,她把目光从父亲脸上转向我,轻轻对我说,没事的方军,你先吃饭。桌上饭菜已经摆好,我一动没动,母亲说你不饿吗?我说不饿。母亲说你陪我吃点。说着来到桌前就要动手拿筷子,就在这时父亲一步跨过来,怒吼一声,把饭桌整个掀翻,这个动作是我都没有想到的,饭菜狼藉一地,母亲怒了,完全是被父亲这一掀激怒的,她像头母狮扑向父亲,双手同时朝父亲抓去。父亲这次一点也没示弱,他开始反击母亲,这一次反击跟以前大不一样,有力度更有凶狠,他没有再去控制母亲肢体,而是放开双手左右开弓打向母亲。
我不知道这一次我为什么没有选择逃跑,勇气从何而来?我本能地冲到他们之间,不顾一切双手抱住父亲,父亲冲我怒吼并挣扎着,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很冲,父亲喝酒了,我说您别跟我妈耍酒疯!他们没有想到我的声音出奇高,父亲愣了一下,又继续在我怀里挣扎,他让我放开手让我别管让他出去,他的语言此刻对我毫无作用,我还是死死抱住他,我担心他把母亲打了,保护母亲这种做法完全是我潜意识迸发出来的。我的力量和执着让父亲更加暴怒,他不顾一切想掰开我双手,却徒劳无用没有任何效果,他吼道,松开我听见没有!我说不松,你把火消了我就松。父亲不说话,一只手朝我打过来,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脑袋也有点蒙,他从我怀里挣脱出去,瞬间把母亲打倒在地,勇气驱使我再次用劲全力把父亲抱住,母亲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摸过一个摔瓣的饭碗向父亲扔去,碗从我耳边飞过划向父亲脖子。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恐怖场景:父亲脖子被碗的破边划出一个大口子,血从脖子上流出来,不,是喷射出来,血不停往外喷流,像火山熔岩,我吓坏了,站在那里浑身发抖,母亲也吓坏了,呆呆站在我身后,场面瞬间平息下来,父亲想用手把它捂住,却毫无意义,血继续向外喷涌,父亲看上去也吓坏了,他紧张而又急促地对我说,快,快弄我去医院儿子!快!
我和母亲没有任何反应,都傻掉了。
父亲有点站立不住,身体开始慢慢往下瘫,他就像一个大大的人形气囊,缓缓而又无力地瘫在地上,父亲仰躺在地上的身躯在我眼前显得格外壮大,他非常痛苦,不停扭动身子想驱散浑身疼痛。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跑出了屋子,她去喊邻居赶紧来帮忙。母亲出去后我感到极度恐怖,父亲看着我,眼神是乞求和绝望的,他努力张着嘴,用手不停指着自己的脖子,我不懂什么意思,血还再不停往外流,像缓缓涌动的熔岩不再那样喷涌而出,很快父亲脑袋和背下都是血了,还在不停涌动的鲜血让我感到了巨大恐怖,我躲在角落里,蹲下身子用双手捂住自己眼睛,不敢再看父亲,我耳边响起父亲的哀求,那哀求声像是梦里,断断续续,一遍又一遍,由强减弱,渐渐在我耳朵里消失掉。
父亲脸色煞白,两只眼睛一动不动直直地望着屋顶,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惧怕他的面容和那双眼睛,我把脸再一次埋在双腿里,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它让我想起那个噩梦,天啊,它们是多么相似啊。
母亲一定是非常后悔,一个人蹲在手术室外面低头抽泣,她的哭声我虽然不能听到,但那不停抖动的身体让我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哭泣正在汹涌澎湃一泻千里。邻居们帮着忙前忙后,至始至终母亲都是一个人蹲在那里,直到警察来把她带走。父亲去世消息母亲是转天早上在派所里听到的,这一消息让她跪在地上久久不起,她说这不是她本意,她没想到会是这样,她在自言自语,忏悔赎罪,一切都是多余了。虽然母亲是误伤导致父亲死亡,但还是被判了刑。母亲在监狱服刑期间,我一个人不敢住在家里,那个家让我非常恐怖,一进到屋里我就看到父亲直勾勾望向屋顶的两只眼睛和那张惨白的面容,这场景仿佛死死印在我脑里,挥也挥不走。
父亲走后,我一直住在姑姑家,她们非常照顾我,每天晚上陪在我身边,看着我入睡。那些日子我睡眠非常不好,每天做恶梦,经常被吓醒,我睁着眼睛不敢再入睡,姑姑说我这是吓坏了,我知道我是很难忘掉那一幕的。
四
后来我知道那天晚上父亲下班回来为什么要在外面喝酒,为什么喝了那么多,他本来是没有太大酒量的,但他还是让自己喝了那么多。母亲一直怀疑父亲还在恋着那个旧情人,而且从来没跟对方断绝过来往。我曾偶尔问过父亲,我问他你现在还跟那个女人有来往吗?父亲说我们没有来往已经有很多年了,虽然有时心里还偶尔想一下,但很快还是放下了这种念头,她也是有家的人了。父亲心情我能理解,即使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也难以忘掉对方,父亲说那个女孩很温柔,从来不会大声讲话,我们谈恋爱时她还在上着电大,她劝我也上,我那会儿刚刚上班,工作也不错,就放弃了那个念头,她平时喜欢画画,只是自己画着玩,还给我画过好些,后来让你妈背着我都给扔掉了,我问过你妈,她不承认,说她不知道,其实我明白就是她给我扔掉的。因为我的出恋,你妈始终怀疑我跟人家还有来往,我去哪里她都对我不放心,我觉得你妈有点神经质。有些事我不该跟你说,你妈经常偷偷翻我提包和口袋,你说哪有一个女人对自己男人这么不放心的。我说你能跟我发誓,现在跟那个女人绝对没有任何来往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父亲这句话,是为了我的母亲吗?父亲说你母亲不相信有情可说,怎么连你也怀疑呢?我说我也不知到为什么。
对父亲的怀疑,母亲已经到了极致,她不止一次偷偷跟踪父亲,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奇怪的是我和父亲竟然都没有任何察觉,父亲每一次被跟踪都浑然不觉,那次夜里我被她们吵醒,就是她跟踪父亲回家后的结果,父亲被跟踪直到死也不知道。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家收拾屋子,在父亲一个写满诗的笔记本里发现过那个女孩写给父亲的一封情书,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我那会儿刚刚记事,印象中父亲喜欢写诗,写的什么诗我不懂,而那封情书恰恰是一首诗。晚上母亲看到父亲回来,拿着那封信问他,是她写给你的吧?母亲没有动怒,也没有激动,脸上还带着淡淡微笑。父亲说那是以前我们在一起时她写的一首诗。母亲说听听,说的多轻巧,还那是我们以前在一起时她写的一首诗?你不用骗我,我不生气,我知道这个不是诗,是你们还在联系的暗号,你以为我不懂吗?父亲笑笑说,既然你都懂,那好,你就给我说说这是什么暗号。母亲冷笑一下说,哦,你想叫我说我就说是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写的什么意思咱俩都知道,你不要跟我装,没意思。父亲说,之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更别说来往,你就是不相信,非得让我说出还有联系你就满意了是吗?母亲说本来你们就是有联系,你还要死不承认。父亲有些恼怒,他说我说过没有联系就是没有联系,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管。我纳闷,那次他们竟然没有爆发战争,而且有好些日子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家里气氛非常融洽。
有一次我背着父亲到他黑色手提包里找烟,偷偷摸摸在父亲手提包里摸烟抽这种行为我只是偶尔为之,每次最多拿两支,多了怕发现,拿烟时我在包里看到一个没打开的避孕套,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懂得了男女之事,知道那是男人用来做什么的。那个避孕套并没让我对父亲产生任何怀疑,我知道那是他跟母亲行房时用的,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忘掉。可是没多久母亲却跟父亲因避孕套事情发生了战争,就是那天父亲在外面喝酒出事的头天晚上,他们没有回避我,母亲似乎有意当着我的面质问父亲,语气平和让父亲解释一下这个避孕套是怎么回事。
父亲从容淡定说,这是咱俩用的有必要解释吗?
母亲说你真拿我当傻子了是吧,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家里有几个,放在哪,用过了几个,我心里一清二楚,你骗不了我。
母亲的话让父亲哑口无言,他看着母亲,表情有些尴尬。
母亲得意地说,你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
父亲说,我能说什么,说什么你都会毫无理由地无限怀疑和不相信,而且你这个人一直对我疑心重重成天怀疑,咱们生活了这么些年,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自己看不出来你有很大问题,我不想说你脑子有问题,但我必须跟你说,你脑子就是有问题,你知道吗?跟你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能把一个正常男人逼疯逼死,好了,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随你便。父亲这一次话出奇多,把没说过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好像要给母亲做一个摊牌一个交代,说过这些话后,父亲便不再说话转身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五
早上醒来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上班,他们是几点走的我不知道,他们走时没有弄出任何声响,那会儿我可能刚刚进入熟睡中,父亲和母亲不在一个单位上班,每天早上父亲都要早于母亲去上班,已成规律,父亲走后母亲会把我的早点弄好再走,那天却一反常态,桌上干干净净一口吃的也没有,我在厨房用大油煎两掺面馒头片那会儿,母亲没有去自己单位,她去了父亲厂子,直接找到厂长,她向厂长介绍自己是谁的家属,以及来这的目的。
母亲走后厂长把父亲叫到他那里,他被厂长约谈了,谈的什么具体多长时间没人知道,晚上下班父亲便直接去了小酒馆,有人看到他一个人在小酒馆里独自饮酒。我后来总在想,如果那天母亲没有发现父亲的避孕套,如果母亲转天没去父亲单位,如果厂长没找父亲谈话,如果父亲没有下班去到小酒馆里喝酒,那天晚上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他还会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现在想想,即使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早晚也要发生呢?所有的如果其实都是不可能有如果的。
父亲后事都是我父亲家的姑姑兄弟姐妹们给忙活的,她们替父亲摆灵堂送路接待前来吊唁的所有亲朋好友,母亲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给父亲吊唁,这是好事,这时候如果母亲那边来人无疑是战争的导火索。我大姨通过一个好朋友给我捎信,算是代表娘家人来给父亲吊唁了,她还让好朋友带来给父亲的买纸钱,我对母亲娘家没有一点怨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姑说母亲是最差的一个女人,她们娘家也是我们方家最差的一个亲家,我完全理解姑姑心情,姑姑让我今后一定要跟母亲娘家断绝亲戚关系,我答了姑姑一定要断绝亲戚关系,但我心里做不到,娘家人毕竟是母亲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怎么能断呢。守灵三天我听到了父亲家跟母亲家许许多多恩怨,父亲家里人让我一定记住杀死父亲的罪魁祸首,我知道父亲的罪魁祸首是母亲,可母亲也没得好,劳教所里并不是人呆的地方,母亲也在承受着良心的谴责跟身体惩罚,她也不好受。告别父亲遗体时姑姑哭的最伤心,几近昏厥。小时听父亲说姑姑是最疼他的,这只是其一,关键是父亲的初恋跟姑姑关系处的最好最融洽,父亲跟她分手后她还跟姑姑有联系,她们像亲姐妹。
我已经记不清我在姑姑家里住了多少天,回到自己家时是姑姑陪我回来的,站在门口看着冷清而又灰尘遍布的屋子,我有一种要哭的欲望,姑姑在一旁拉了我一把说,来咱俩一起把屋子收拾收拾。那天晚上姑姑说她不走了,陪我在这里,我不想让她陪我但又非常希望她能留下来,我不敢一个人住在这个屋里,我对这屋里的一切都感到恐怖,姑姑一定能知道我的感觉。一会儿你姑父也过来,今晚我们两个人都在这里陪你,你放心吧。姑姑一边忙着扫地擦桌子,一边安慰我。我看到椅子腿上有一块不大的血斑,血斑早已经凝固,但我还是看到了,那是父亲的血,虽然已经很久但还是那种血红色的,姑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偏偏让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潜意识里要寻找?还是父亲的灵魂在昭示?一踏进这个屋子我就想起了父亲,我不能看到这个屋里的所有一切。门后有一个父亲穿了一两年的裤子,那条裤子上还有母亲给他亲手缝过的针线,裤子有些脏,母亲还没来得及洗,我们的衣服都是由母亲洗,父亲有时想替母亲不让,说他洗不干净,每一次母亲洗完衣服都要用熨斗一件一件烫好,整整齐齐码放到柜子里,她聚精会猫腰给我们烫衣服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那个画面让我温馨又伤感。
你在那想什么了方军?姑姑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
六
在我整个回忆和讲述中,他始终安静地看着我,偶尔会露出一些微笑,我说我在回忆这些事情时候,您可能看得出来我的情绪是紧张和难受的,实际上我也在努力控制着可就是无法做到。他说不要紧慢慢来这很正常,你可以喝口水缓解一下。他的微笑始终让我感到温馨舒服,我说是不是我讲的时间有点长了?他诊室门外还有病人再等候,他说不要紧你可以继续。我想抽支烟,他犹豫一下还是允许了,走到窗边把窗户轻轻打开一条缝,又找来一个小玻璃药瓶放到我面前示意把烟灰弹到那里面,他看着我把烟点着说,只能抽一次。我说谢谢。烟让我慢慢舒缓下来。
母亲出狱时我已成家有了一个儿子,她在里面总共服刑十一年,罪行是过失致人死亡。母亲苍老很多,头发几乎花白,姑姑给我们操办完婚礼后我带着郭燕去看过她,在探视大厅她跟郭燕隔着透明玻璃第一次见面,她看着郭燕淡淡地说你就是郭燕?郭燕轻轻点点头喊了声妈。母亲笑了,她笑得并不幸福也不自然,有内疚跟苦涩在里面,你跟方军两个人一定要好好过日子,嫁给他一定要好好爱他,不要怀疑。母亲跟父亲情况郭燕都知道,她点头笑笑说,您放心我会的。那次探视时间很短,母亲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郭燕路上问我,你说你妈会后悔吗?我说这还用问,亲手把自己爱人杀死了,不管她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会后悔一辈子的。我想起小时父亲的很多事情,想起了父亲给我买的那个足球,郭燕说你爸是一个好父亲,你以后也应该向他学习。我没说话。
母亲回来后,我计划还让她住在那间老房里,母亲不同意,说她一天也不想再在那里住,郭燕说那间房子我们没住过一直给您留着呢,郭燕理解不了母亲心情,我说咱们把它卖掉再给您买一间,母亲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很快我就给老房子卖掉又在附近买了一间,搬家时母亲让我把父亲所有用过的东西扔掉,只留下她和父亲一张结婚照,照片是人工彩色的,母亲把头歪向父亲肩膀,虽然没有挨到,但已经非常近了。父亲笑的有点严肃,而母亲却笑得很幸福。母亲说这是她们结婚前姑姑带他们去照相馆照的,我自言自语说,那会儿你们看上去很幸福,母亲没说话手里拿着那张相片,有眼泪滴到上面。那张相片母亲一直用镜框镶着挂在新房里,有一次我去看她,发现她枕头下压着那张相框,看得出她是慌忙中放到下面去的,她可能怕我看到坐到床边用身体挡住,我怕她尴尬,装做没看见,她说你没有什么事就回去吧,我这挺好,她催我赶紧走的目的我清楚。我要出门时候母亲把我喊住了,我说您还有事吗?她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说,还有三天是他的日子,她没有说出忌日,我说纸什么的我都买好了。母亲说替我也买一份好吗?母亲这样的口气从来没有过,我说行。
那是母亲出狱后父亲第一个忌日。
酒我给买了,母亲说,是他最爱喝的大曲。母亲买了两瓶让我给带去。
七
母亲一直睡眠不好,经常半夜醒来,有时坐在床上瞪着两只眼睛,有时在地上来回溜达,她说她一到下半夜三点来钟就醒了,再怎么睡也睡不着。我想起父亲那晚在医院抢救时的场景,他浑身是血躺在急诊室里的四轮急救车上,好几个护士和大夫围着父亲忙得手忙脚乱,心电图,吊针,创伤处理几乎同时进行,我跟几个邻居站在门口看着,身体虽然被杨姨紧紧搂着,她一定还能感到我不停轻轻颤抖的身体,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惊恐看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个大夫朝我们走来,他摘掉口罩问谁是病人家属,我下意识用手指指自己,杨姨说这是他儿子。大夫说要找病人家属。杨姨说被警察带走了。大夫看着我和杨姨说病人因伤及到大动脉失血过多,我们一直在做抢救,你们也都看到了,人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我像个木头已经麻木到没有任何反应,觉得身体被杨姨紧紧搂了一下。父亲眼睛一直是紧闭的,我把眼睛从他脸上慢慢移开,看到急诊室挂钟已经是下半夜三点,父亲的生命最终停止在这个时间上。我不知道母亲每晚三点醒来会不会源于父亲在这个时候的召唤?我没把父亲停止心跳时间告诉母亲。我对母亲说我带您去医院看看吧。母亲说不用,只是睡不好觉,心里又不难受。我说要不您跟我们住段时间。母亲说自己习惯一个人住了。可能怕给我们麻烦,不想影响我们生活,我跟她提过多次都被拒绝。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晚上能陪我住一宿吗?我说没问题,我们三口都去陪您。她说不用,你一个人过来就行。那天晚上我跟母亲两个人一起在家吃的饭,我炒了两个她平时最爱吃的菜,一个是素炒青椒,是那种最辣的;一个是蛋炒番茄。
我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母亲一边吃一边说,在里面那几年就想吃这两口。
我看着她香喷喷地吃着,犹豫一下说,这两个菜是我爸最拿手的,我还是跟他学的。
母亲停下筷子,把脸转向我,看了我一会说,还恨我吗?
我没说话,不知该如何对她说,她可能看出我心情,说我不要求你回答我,只是想问问你,我知道是多余的。她往我碗里夹了点菜,你也多吃点吧。
这两样菜是父亲经常给母亲炒的,素炒青椒时,父亲要多放一些盐,他知道母亲口重,有一次母亲夹了一口父亲刚刚端上来的素炒青椒说,盐放少了吧?今天有点淡。父亲二话不说马上端回去重新放盐。母亲吃菜口味父亲把握特别好,每次都能做到恰到好处。母亲让我跟她分床睡,我没同意,我说我是您儿子为什么要分床?母亲说我夜里睡不好怕影响你。我说我没事。母亲说那也不行。她为什么不让我跟她睡在一个床上其实我隐约也能够感觉到,她怕想起父亲如果我没猜错,母亲说过我有太多地方像父亲,比如长相,比如声音,比如动作,就连说话口气她说也特别像。
母亲说她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那咱都早睡吧,我说。
母亲关掉灯。
屋里黑下来,我们谁都不再说话。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阵哭泣声惊醒,那是母亲在梦里的哭泣,声音巨大难以控制,我打开灯推醒母亲,她愣愣地看着我,我把你给吵醒了是吧?她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我说您做梦了?母亲点下头说她每天都这样。她没说梦的内容,我也没问,那些梦的内容我完全能够想象到。母亲坐起身子,低着头,悲伤似乎还在他心里发酵,我倒杯水给她,她接过去但却一口没喝,我说把杯里水喝了睡吧。她摆摆手又用手擦擦眼睛,我坐在床边悄悄陪着她。母亲说今天本以为你在这我能睡个好觉,没想到还是......我说您每天都是这样吗?母亲说因为你在这陪我今天好多了。
我觉得您必须到医院看看去了,这样下去不是好事。我预感到母亲如果照这样下去身体会出问题。她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抬起头说,那你明天就带我去吧。早上我醒来时看到母亲还在床上呆呆坐着,她一直没有睡,我说您这样下去真会出问题。
我在医院给母亲挂了心脑科,她这两样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看看。我们去的早,很快就看完,大夫给母亲的结果是:神经衰弱跟早期精神抑郁,我背着母亲问大夫严重吗?大夫说抑郁症这种病如果平时不好好控制会发展很快,严格说你母亲已经到了轻重度。我把母亲情况跟郭燕说了,她说你说怎么办?我说我先陪她住些天看看再说,如果不行咱们一起住到她那。郭燕说你爸爸的死对你妈妈影响这么大?
八
在母亲家住了三天她就有点烦了,让我回家住去,我说那您得跟我一起回去,她说那样你们不方便,我说两间屋子有什么不方便。她看着墙上结婚照,自语着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让你们操心了。我没说话陪她一起看照片,镜框里相片已经有些变旧,人工上色也变得失去原有面貌,但玻璃却非常干净明亮,她把脸转向我,看着我说,郭燕对你还好吗?我不明白她这会儿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我说郭燕对我很好您放心。
她是你的初恋吧?
我说是的。
这是你的幸运。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因为你是男人不会明白。
是吗?我看着她,一脸疑惑。
母亲轻轻叹口气说,你们男人永远都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女人,女人的死穴在哪你们不会知道。
我很了解郭燕。
妈告你一句,你要好好珍惜和对待郭燕,要洁身自好,你这样做看似为了郭燕,其实最终是为你自己,你一定要牢记妈妈这些话,就是我以后不在这个世上了,你也要记着我的话。她的表情让我莫名其妙。
您今天怎么了?我问。
母亲说没怎么着,妈今天就想跟你说说这些话,除了他你就是我最爱的人。自从父亲走后母亲每提到父亲都用“他”来代替,我能理解。
母亲这些话我一直牢记于心,但又始终不解其意。为什么她要跟我说这些话?为什么让我一定要牢记?母亲不让我再陪她,把我轰走了,这一次我顺从了她,她说我不走她就自己睡马路上去,跟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她的性格脾气我太了解了。大概有半年多,母亲食欲开始减退,精神也开始萎靡不振,我每次去给她变着花样做饭她也只吃两口,她说她不想吃东西,一点食欲没有。我去药店买了一些开胃消食药给她吃也不管用,我背着母亲去医院找那次给她看病的那个大夫问是怎么回事。大夫说这是抑郁症的重度表现,没有食欲,精神萎靡,极度厌世,这些母亲现在都有了表现。她曾跟我说起过许多次生活没意思活着没劲的话,我以为母亲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跟郭燕说我替我妈看过大夫,大夫说这种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险,每天必须有人陪护,不然病人随时都有轻生可能。郭燕跟我一样明显感到了害怕,她说明天咱们一家都住在你妈家里,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说我也是这个想法,明天咱们一早就去。
那天早上我们三口在母亲家看到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掉的画面:母亲倒在地上割腕自杀了……
那个场面不知为什么让我莫名其妙的平静,郭燕尖叫着扭头跑掉了,儿子却蹲在地上不敢再看,他多像那时的我啊。
我看着对面心理医生,我说我现在心脏难受,不想再讲下去可以吗?他说你不要紧张,闭上眼睛,跟我一起做深呼吸。他带着我开始轻轻深呼气,一下,两下......我看到了涌动的熔岩,是那种鲜红色的……
-

- 10块钱买的琥珀,一百块卖掉,赚了九倍(10块钱买的琥珀,一百块卖掉,赚了九倍
-
2024-04-27 04:54:32
-

- 五人出游三人藏尸冰柜案背后:邪教全能神组织洗脑全揭秘
-
2024-04-27 04:52:28
-

- 三人藏尸冰柜案背后:死者生前曾入邪教 洗脑过程揭秘
-
2024-04-27 04:50:25
-

- 故事:教学楼5楼密封了20年,有人误闯后,学校开始怪事连连
-
2024-04-27 04:48:21
-

- 公交车上遇见个女孩,以为桃花运,结果...(胆小慎入)1
-
2024-04-27 04:46:18
-

- 故事初恋失败我不相信爱情,和大八岁男神相处3月,却再次动心(知乎上很火的
-
2024-04-27 04:44:14
-

- 全本八扇屏文本
-
2024-04-27 04:42:10
-

- 三分钟小故事(三分钟小故事幼儿)
-
2024-04-27 04:40:07
-

- 杨过爱的一直都是郭芙(杨过为什么爱郭芙)
-
2024-04-27 04:38:03
-

- 每日鬼故事-荒村鬼影(荒村鬼事一个人一个鬼故事)
-
2024-04-27 04:36:00
-

- 16个民间灵异故事集,高速冤魂、冥婚……相信我,你们会喜欢的
-
2024-04-27 04:33:56
-

- 民间真实老故事(民间真实老故事300字)
-
2024-04-27 04:31:53
-

- 汉瑶乡儿童失踪事件(小说)
-
2024-04-27 04:29:49
-

- 我八岁被娘卖给病夫做童养媳,后来我被倒手卖了三回。
-
2024-04-27 04:27:45
-

-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50篇(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
2024-04-27 04:25:41
-

-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100篇(上)(历史人物故事大全100 中国历史)
-
2024-04-27 04:23:37
-

- 故事:失眠的我点了个哄睡小哥,可他怎么是我继父的儿子?
-
2024-04-27 04:21:34
-

- 刘驼子讲鬼故事:农村怪事
-
2024-04-27 04:19:30
-

- 五分钟看完一部穿越小说~快穿:校园惊魂 (人工智能缩减版)
-
2024-04-27 04:17:26
-

- 故事:我27岁时母亲上门逼婚,隔壁男神推门“阿姨我是她男友”
-
2024-04-27 04:1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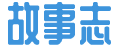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赛罗奥特曼睡前故事30篇
赛罗奥特曼睡前故事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