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烨为什么能容忍英儿?顾城和妻子谢烨的爱情故事告诉你答案
谢烨为什么能容忍英儿?顾城和妻子谢烨的爱情故事告诉你答案
1993年10月8日,顾城对着背向自己的妻子谢烨举起了斧子。
银光遍洒,阳光照耀在斧刃上,满满都是残忍的坚决。
谢烨当场血流如注,躺倒在地,脸上写满了错愕,可是头部遭受了重击的她再也无力挣扎,虽然未一时毙命,但睁大的双眼看着手持利斧的顾城,眼前却渐渐模糊。
可是顾城却好像早就耗尽了所有的气力,他把斧子一扔,跑到了姐姐顾乡的家,开口就是:“我把谢烨打了。”
他们的感情早就出现了问题,撕扯、争执甚至是扭打,顾乡并未多想,只是急忙跑去了顾城家去看弟媳,见到的却是血流满地,倒地昏迷的谢烨。

我把谢烨打了——顾城说这句话的时候,脸色铁青,恍若梦游,眼神直愣愣的。
他的魂已经没了。
顾乡意识到了不对。看着倒地的谢烨,她左右支拙,没了章法,她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跑回家去看顾城。
她不知道顾城会做什么,对于这个任性的弟弟,做出什么来,她都不觉得奇怪。
可是等她回到家,见到的却是用电话线自缢在自家后院的树上的弟弟,已然毙命。
而谢烨被送到医院,经过数小时的抢救,还是因为伤重,最终身亡。
自此,这对曾经被视为金童玉女的夫妻,双双离开了人世。留下的,除了不满五岁的儿子,还有伤心欲绝的父母。
顾城曾说,他们两个离开了彼此就没法活下去。换言之,顾城把谢烨视作了自己的命。
可是谢烨那天和顾城说,她要离婚,这无疑是谢烨把他的半条命给拿走了。
世人皆以为是谢烨的红杏出墙才造就了这场悲剧。
毕竟是她提离婚在先,毕竟是她要和一个叫做大渝的男人私奔。
可没人想想,谢烨才是那个受害者,谢烨才是那个在这段爱情里付出了全部的人。

她早就已经累了,她就像个老妈子,背着顾城这个巨婴,十几年含辛茹苦照顾着顾城。她可以忍受顾城像个孩子:撒泼耍赖,甚至埋怨她把爱都给了儿子桑木耳;她也可以把儿子送给毛利人抚养,她也可以带回丈夫心心念好久的那个英儿,甚至连丈夫对英儿说“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雷(谢烨)不一样,雷是我造就的。”她也可以假装无动于衷。
但是她终究是一个女人,她终究是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
她可以把顾城宠得如同生活在童话里一样,可她自己终归还是清醒的。她清醒地用一切所能够做到的纵容,去维持顾城童话般的梦境。
可她还是会累的,会倦的,她没有那么强大,十几年的宠溺早就让她精疲力竭,尤其是当丈夫在情人离开以后那种毫不廉耻地怀念,甚至还写了一本小说《英儿》,而记录者正是她自己。
她崩溃了。

所以当大渝出现了,并且如同她迷恋崇拜顾城一般迷恋着她,她心动了。
她想着或许可以试试,或许试试这没有顾城的日子。
她心中产生一种渴望,甚至后来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还给大渝找好了房子,并通知顾城,自己要离婚了。
她满心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试试没有顾城的日子了。
或许她心里还抱着回来的准备,因为就在惨案发生的几天前,她还同顾乡说,自己还是深爱着顾城的。
她或许只是一种尝试,可是这种尝试却成了压倒顾城的最后一根稻草。
诗人杨炼曾说:
顾城构建了一个表面的童话,而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深刻的孤独感,还有错裂和错位的感受。
顾城就像是个表面精致的气球,内里全是杂乱不可靠的氢气,一旦受到威胁,就会爆炸。
其实这种“表面的童话”早在儿子小木耳出生开始就出现了裂痕。顾城对于儿子的态度让谢烨第一次了解了诗人内心的纯粹精神王国的虚妄以及残忍,直到英儿的介入以及离开,这个童话已然是摇摇欲坠,等到大渝的出现,那个能够给谢烨一份正常生活的男人来到了谢烨面前,她再也没了气力去陪着顾城维持这看似美好实则虚妄的精神王国了!
于是一把死亡的屠刀最终劈向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顾城留下过遗书,就在他拿斧头劈向妻子谢烨,并用电话绳吊死自己的几个月以前。
这封遗书写得很早,是谢烨最后一次回到激流岛,带给姐姐顾乡的。
顾乡记得当时谢烨的表情很是不屑,她向来是站在弟媳这边的,所以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没怎么细看,就扔到了桌子里,只是依稀记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简单而深不可测每个事情都是这样,我不知上天为何如此只被它的残忍和微妙之感惊呆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在这份信件下面还有四封凌乱的遗书。其中一封还可以看出来是一封家信,只是不知怎么划出一条突兀的横线,抬头处加上个姐字:
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
烨许多事一直瞒我......
然后交代后事:
......
我的手稿照片,由老顾乡清理、保存;房子遗产归木耳;稿费、《英》书稿拍卖的钱寄北京的给老妈妈养老;书中现金老顾乡用于办后事。
不要太伤心,人生如此。
老妈妈万万要保重。老顾乡多尽心了。
顾城 Gu Cheng
其他的几封信分别是给母亲、姐姐还有儿子木耳的。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道:
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
木耳,我今天最后去看你,当马给你骑,我们都开心。可是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你,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愿你别太像我,像什么呢?
可能顾城心里也知道他自己那种孤独、虚妄的精神世界。
世界很大,他很小。
所以他希望儿子做个平实的人,他看透了自己世界的满目疮痍。
他知道自己没救了,因此他艳羡并希望儿子可以继续活下去。
但他本还可以活下去的,只是他不要了,这种生活他不要了,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而这全因为谢烨。
他就像是一只树懒,爬在谢烨身上汲取了十几年的树汁,而现在这棵树死了,他也就活不下了。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而这种希望的接续或者说毁灭,其实遇到英儿的时候,便出现了崩塌。
1986 年,北京昌平诗会,30 岁的顾城和 23 岁的李英相识。
他在台上读诗,她在台下凝视。
李英是顾城的崇拜者,是死忠粉。
每次见到顾城,李英都说,“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晚上谢烨和李英,还有文昕住在一个宿舍,谢烨和她们聊自己和顾城那如同传奇一般的恋爱故事,以及关于顾城的各种趣闻轶事。
文昕说,每次李英听到感动的地方都会把自己蒙在被子里。
泣不成声。
或许从那时候开始,李英对顾城就对了更多的复杂的情愫。
而这种情愫在顾城后来加入他们的小团体后,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她在后来给文昕的一封信中,这么写:
我爱上顾城了,爱得恨不得为他去死。
后来顾城要和谢烨去德国了,李英开始悲伤了。
她怕顾城一去不回,她怕自己心中那隐藏的情愫自此死亡。
她和文昕说,我要去表白。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然后她就一个人去找了顾城。
一进门,她就当着谢烨的面,和顾城表白。
她说自己对顾城的崇拜,她说自己对于顾城那种禁忌的爱。
她忘乎所以,全然没有谢烨在一旁的自觉。
顾城懵了,可是谢烨在一旁只是翻看一本杂志。
他们说了一晚上,谢烨的杂志就翻了一晚上。
谢烨以为自己和顾城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可是这中间后来因为有了李英,从此便有了嫌隙。
到了新西兰以后,顾城依然和李英有通信。
他饥渴地向李英表示自己内心的欲望,他毫不避讳自己的妻子,甚至谢烨还在纵容着他的这种行为。
而在到了激流岛上后的1990年,谢烨还买了机票,让李英来到了激流岛,并在岛上呆了两年。
自此他们开始了一种匪夷所思的三人行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甚至得到了谢烨的默许。
她好像完全不在意,有一次她还兴高采烈地和顾乡说他们的三人行,顾乡十分震惊地说:“顾城这样子怎么可以?”
谢烨反而不在乎地回答:“他也没怎么样?”
他是没怎么样,因为在谢烨看来,只要顾城还有一份心在她这里,她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并没有。
1992年3月,顾城和谢烨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工作一年,而李英却在他们去德国后的几个月,不知所踪。
据说她和岛上一个英国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不管结果怎么样,李英终究是抛弃了他们的小家庭。
顾城曾给文昕的信中这么描述英儿的离去:
一个岛也会骗我,我回来的时候,她没有了。
她没有了,顾城陷入了无比的绝望。
谢烨本以为英儿的离去会让顾城彻底回到他的身边,可还是没有。
他对英儿有着无比的眷恋以及怀念,哪怕是她抛弃了他,可他心中英儿却始终是那个和他灵与肉交融的另一个自己。
不仅是爱,不仅是性。
他对谢烨说我要写一本小说,写一本叫做英儿的小说。
谢烨说,你写吧,我来记录。
于是他在书里描写:
我触摸你的皮肤,倾听你内心深处的愿望。你表达着自己,告诉我你简单的身体后面无法掩藏的秘密,你独自起伏像冲击海岸的春天的潮水。
是这样的时刻,我放任自己,在爱情和欲望里吸吮着你。
谢烨终究还是介怀了,沉默不语,走开去。
可是顾城毫不收敛,他继续写,甚至还反复和谢烨说:
“你不知道,我那时要在北京不走,英儿是可以和我一起死的。”
“她说第一眼看见我,她的命就注定了,她的日子从此被那一刻挡住,没法再继续了......”
他说他想死,因为英儿走了,带走了他的灵与肉。
可是这“灵与肉”的称谓是他曾经用来称呼谢烨的呀。
她怎么能不在乎?!
爱是占有。是私欲。
可顾城说他想死,她又怎么舍得。
他曾经给李英打过电话,可是接起电话的时候,是个男人的声音,他又忙不迭挂了。
后来他又说要写一本叫做“英儿”的书,她只能答应,因为她太害怕他一直在那里说死了。
可是小说开写了,她却后悔了。
她听着顾城在那里说着他和英儿的爱欲,说着他们的情比天高。
她仿佛成了局外人?!
后来,小说写完了。顾城好像平静下来了。他和谢烨说,我们把小木耳接回来吧,我们好好生活。
谢烨却说:一切都晚了。
一切都晚了。当发泄完情绪的顾城回过头想要再次牵起妻子的手,却发现她早已经回不去了。
一切和爱有关,一切都从爱开始。
谢烨想要的从来都是平静的生活。
可是顾城给不了。
但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谢烨不知道。
那个最初的传奇,总是用最美好的词汇被人们讲起。
那是1979年的夏天,顾城坐火车从上海回北京,谢烨则是到承德看望父亲。
他们的座位紧挨着,到了南京站,别人占了谢烨的座位,她没说话只是站着。站在顾城的身边。
她的头发很长,发梢带着阳光,像一只调皮的鸟儿,随意地点在顾城的脸颊。
顾城的心里紧张极了。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带着光环的女孩了,只是他不敢直勾勾看着她。
她亮得耀眼,让他不敢直视。
就像他后来在给谢烨的情书中写的那样:
我开始感到你、你颈后飘动的细微的头发。我拿出画画的笔,画了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满脸晦气的化工厂青年。我画了你身边每一个人,但却没有画你。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
后来到了晚上,顾城终于鼓起勇气和谢烨搭讪。
他们开始说话。
他给她念诗。
那个年代,诗真的是到哪里都通用的法宝。
他们从深夜聊到启明星升起。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车厢的时候,顾城意识到,倘若再不做点什么,这一切终将会失去。
终将会成为内心的一点涟漪。
他不甘心,甚至觉得愤怒。
他鼓起勇气,掏出一张纸条,写下了自己在北京的住址。
他没想到这个无意栽下的种子,后来竟然真的开花了。
那晚的畅聊给谢烨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回上海的时候,路过北京,她竟然鬼使神差地下了车,挨家挨户真的找到了顾城家。
敲开门的时候,她就看见了一脸错愕的顾城。
像是命中注定。
也像是无可取代。
因缘际会,就像是两个人的劫。
他们在院子里开始聊天。
他们谈哲学。
他们聊诗。
一切就像是那个在火车里的晚上。
浪漫,又像是童话故事。
临走前,谢烨给了她在上海的地址。
没有离别的伤心,因为他们知道离别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他们开始疯狂地通信,从1979年到1982年,他们给对方写了相当于两部长篇小说的情书。
顾城甚至还在信里孩子气地问:
“我们在火车上相识,你妈妈会说我是坏人吗?”
然而谢烨的母亲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父母总是现实的,因为顾城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连工作的打算都没有。她将顾城认作是个不靠谱的对象。
于是当顾城追随谢烨的脚步来到上海的时候,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但是顾城不管这些。他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所以尽管因为世俗牵扯了他逐爱的脚步,但是在这种压力下他并没有被击倒。
他开始奋力写诗,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谢烨。他笔耕不缀,连最偏远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手稿。
甚至为了让谢烨父母同意,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鬼主意,弄了个木箱子,就放在谢烨家门口,天天睡在这里。
后来逼得谢烨父母没办法,只好同意他们在一起,可是有个要求,顾城必须去精神病医院做个检查。他们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女婿不是个正常人。
顾城虽然觉得自尊心很受伤害,但是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仍然同意了。
结果,顾城在医院里同医生大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医生都震住了,医生欣然宣布,顾城是个正常人。
他对顾城也是佩服极了。
后来顾城和谢烨终于结婚了。
可是这一切,却全是谢烨灾难的开始。
顾城是个靠灵魂活着的人。
除了诗,他什么都不会。
他不会做家务。
他的衣服泡在水里好几天,拎起来,说“水会净化污垢”,于是就算洗干净了。
他的经典伙食是排骨青菜面,他先是烧上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儿,之后再放入整棵整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还自诩为营养烹调。只有谢烨在的时候,才会把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他什么都不会,他只能靠着别人。
没有谢烨以前,他靠着父母,姐姐。
后来遇见了谢烨,谢烨就成了他的监护人。
谢烨不仅要管他的投稿、诗集整理、出版、翻译、版权代理、交朋接友、对外接洽,还要管他袜子放在哪里,指甲有没有剪干净。
谢烨不在,他就无法出门。
后来他们去新西兰激流岛,他们又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王国。
他们在岛上劳作、养鸡、摆摊、画画还有写作。可是除了写作,所有的一切都是谢烨做的。
谢烨太苦了,她就像是个老妈子,要照顾到顾城的方方面面。
甚至在后来谢烨生孩子,大出血。他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写:
“谢烨大出血......真有孤单之感......”
舒婷说,谢烨怎么能够忍下去,她早就应该离开了。
可是她忍下去了,甚至为了顾城,她还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毛利人抚养。
她还要时刻接受顾城匪夷所思的要求:
他要谢烨不打扮,不能剪头发,不能戴耳环和项链,不能穿泳衣,不能和男性过从甚密,不能离开,不能阻止他找第三者,不能有负面情绪......
她就是顾城的保姆,也是顾城永不背叛的缪斯。
刚开始谢烨还能忍受,后来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原因很多,桩桩件件。
他们一直都为钱发愁。
经济上的困厄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那时候,顾城没工作,只是写诗。可是能够得到的稿费也只有一元两元,连吃饭也不够。
后来谢烨还把在上海街道厂的工作给辞了。
两人都是无业游民。
有一次顾城得到一笔50元的稿费,两口子高兴坏了,手拉着手去银行存钱。
可是第二天,白菜降价了,他们欣喜地要囤积,于是去取了10元钱。
第三天,轮胎爆了,他们又去取了10元钱。
第四天,银行的柜台时候,要不然你们把钱都取走吧。
他们一生都贫困无比。
在国内是,在国外也是。
有一次,顾城去参加诗会。顾城问,能不能把谢烨也带上,组织者说不能。
于是,全程顾城都闷闷不乐的。就连吃饭的时候,他都看着饭菜唉声叹气。
舒婷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一想到谢烨在家里连鸡蛋都吃不到,就吃不下饭。
舒婷说,他们一辈子都在为钱发愁。
马悦然说,顾城一无所有。
他们确实一无所有,但是那时他们幸好还有彼此。
他们在激流岛买了一块地,拼命构建了那个童话的王国,因为他们想要逃离这个世俗的世界。
可是那个王国,还是世俗的呀。
他们要还银行的贷款,因为买的地是分期付款的。
他们还要给当地酋长缴税,因为交不上税,他们就会被认为没有能力抚养儿子。
于是夫妻俩,相依为命,情系彼此,竭尽全力想要构筑这个王国。
可是这一切都在儿子出生以后,改变了。
顾城觉得木耳的出生,分走了谢烨的爱。
他甚至连碰都不愿意碰儿子一下,只是躲得远远的,看着顾城给儿子喂奶,唱着摇篮曲。
他不满,因为他觉得这些本来属于他的。
有一次,谢烨要外出工作,让顾城把家里留下的蛋糕给儿子吃。
可是等到晚上回到家,谢烨却发现顾城自己把蛋糕吃了,儿子在一旁饿得直哭。
还有次,舒婷和他们一起出去逛街。在一个小店,谢烨看到一个小玩具,想要买给儿子。
可是顾城不愿意。
他表达拒绝的方式不是说不,或者直接甩脸子。
而是采取了一种极其可笑而又幼稚的方法——他坐在地上,耍起了无赖。要多尴尬,就要多尴尬。
舒婷看得一脸震惊,谢烨却说随他去,不要管他。
直到舒婷说:“我买了,我送给小木耳。我买了。”顾城方才从地上爬起。
他不同意,是因为他不想让妻子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木耳身上。
他要独占谢烨所有的爱。
可是那时候的谢烨已经累了,她觉得自己就是在照顾两个孩子,一个几岁,一个36岁。
她心中的苦没人可以倾诉。
舒婷说她好几次看见谢烨在那里偷偷哭泣。
谢烨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啊。
她也需要爱。
大渝出现了。
在谢烨最需要爱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给好了她离开的理由。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抛弃的,尽管那十几年的爱是那么轰动,她也愿意从头再来。
可是她不知道这次抉择的竟然会如此惨烈。
其实命运早就标注好了代价。
所有所谓的抉择,其实大多数都是没有抉择。
顾城没了英儿,现在他又要没了谢烨。
路是他自己选的,可是他索性哪一条都不选。
没人真正地走进过他的内心,他乖顺的外表里其实埋藏着如同火一般炽烈灼热的情感。
他的气球早就要爆炸,他的世界早就要破灭了,他的王国已然毁灭。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他的遗书写给了顾乡,写给了父母,写给了小木耳,可是就是没有给谢烨的。
因为在这一刻,他的心中认为谢烨和他是一样的,也是要离开的。
他带着太多毁灭的气息了,这种气息不但带走了他自己,也带走了谢烨。
于是就像他在自己的那首《墓床》写的那样: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于是一切都成了真。
一切都尘埃落定。
一切都无从改变。
一切都早已注定。
很多人都奇怪顾城为什么总是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
其实那不过是种保护。是一种逃避。
他说,帽子是他的家。戴上了,世界就和他无关了。
“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
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
它像我的家。
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帽子外就是他从来不愿意去面对的这个世界,他怯懦、胆小、任性。他状若疯狂地想要和谢烨构建一个痴妄的城堡。
可是后来城堡崩塌了,顾城说:真是每一寸都杀我,摸一摸都疼。
于是他不愿意伪装了,他把自己血淋淋地从帽子后面显露出来,绝望地抓住了一只死去的蝴蝶。
而那只蝴蝶就是谢烨。
-

- 美女秘书(现代故事)
-
2024-01-22 23:02:45
-

- DNF鬼剑士男(职业背景故事)
-
2024-01-22 23:00:22
-

- 三种视角讲述博尔特打破百米短跑世界纪录的故事
-
2024-01-22 22:58:00
-

- 美女革命家曾志的悲伤婚姻故事
-
2024-01-22 22:55:37
-

- “大义”的继承者上杉景胜:上杉谦信之后上杉家的故事
-
2024-01-22 22:53:14
-

- 故事:爱上邻国太子,我苦求父皇赐婚,如愿成皇后,却再不敢见他
-
2024-01-22 22:50:51
-

- 文化栾城丨解放栾城与背后的传奇故事
-
2024-01-22 22:48:29
-

- DNF 十二使徒背景故事总汇
-
2024-01-22 22:46:06
-

- 琴师(民间故事)
-
2024-01-22 22:43:43
-

- 故事:她贵为皇后被专宠七年,直到一朝失宠,才知皇帝另有真爱
-
2024-01-22 22:41:20
-

- 别抄袭了,我自己发,传奇虎王拉贾,那个杀牛魔王的故事
-
2024-01-22 22:38:58
-

- 短篇故事十篇:唯美甜蜜浪漫爱情
-
2024-01-22 22:36:35
-

- 故事:25岁生日那天,我不慎被30楼坠落的人砸中
-
2024-01-22 22:34:12
-

- 生命传奇:物种大爆发与物种大灭绝,背后的故事
-
2024-01-22 22:31:49
-

- 200多年的包头故事,你知道多少?
-
2024-01-22 22:29:27
-

- 每况愈下的成语故事及解释
-
2024-01-12 00:58:24
-

- 狐假虎威寓言故事原文_寓言故事
-
2024-01-22 22:29:02
-

- 小学生英语寓言故事:井底之蛙
-
2024-01-12 00:52:53
-

- 莫扎特小时候的故事
-
2024-01-12 00:50:07
-

- 管理者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待新员工:录音机与磁带的故事
-
2024-01-12 00:4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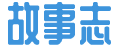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儿童故事小兔子拔萝卜20篇 三只小猪儿童睡前故事34篇
三只小猪儿童睡前故事3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