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爆发的鼠疫究竟有多恐怖?对明朝灭亡有多大影响?
崇祯六年爆发的鼠疫究竟有多恐怖?对明朝灭亡有多大影响?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明朝的灭亡,明朝自身的问题固然是主因,但明末的天灾和气候异常同样极为致命,尤其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这场持续长达十年、波及陕晋、华北数省的鼠疫,更是成为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这场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对明朝的灭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天灾人祸和气候异常,乃是这场瘟疫的主要原因
根据华北地区明末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的记载,上交大历史学教授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中写道: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这场瘟疫的原因,现代研究普遍认为与气候异常和生态破坏有关。
首先是持续干旱。受“明清小冰期”影响,明末时期的降水线明显南移,导致北方开始出现大面积持续性干旱,崇祯年间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不仅湖泊干涸,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
如此大规模的干旱,对于明朝这种传统农业大国,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干旱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极大打击,而且导致了水源的急速减少,增加了人畜混用水源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人感染瘟疫的风险。
其次是大规模蝗灾。现代研究表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因此旱灾的爆发反而更加有利于蝗虫的繁殖,而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根据涂斌《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遭受蝗灾的总数达到了967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如果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则更高。
尤其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在《明史》中,旱灾伴随蝗灾的记载,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例如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
这个景象到底有多恐怖,仅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的为例,当时“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结果便是”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最后是人祸。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再度频繁发生战争,结果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进而导致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致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本就因气候变化失去了食物来源的老鼠,为了生存,开始大量进入人类聚居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
与此同时,由于明朝后期统治层面的问题,底层百姓大量破产,百姓们为了生存几乎将所有能吃的都充入腹中,甚至包括老鼠,这同样极大的增加了感染鼠疫的风险。此外,流民的持续暴增,还会导致瘟疫迅速向外蔓延。
如上所述,由于明末时期的天灾人祸和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了致命打击,不仅导致大量流民的产生,同时也极大增加了老鼠与人接触的概率,而这皆是后来鼠疫的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四年,鼠疫迅速席卷北方各地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从嘉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便开始不断出现瘟疫。不过,彼时的瘟疫多呈现点状分布,虽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危害,但并没有大面积的爆发,因此关于这些瘟疫多见于地方志。

我们仅以山西为例,根据《山西通志》的记载,“嘉靖三十九年……石州(今山西吕梁)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饿盈野”;
“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
“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
“万历十四年,泽(今山西晋城)之州县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间老稚剥树皮以食,疠疫大兴,死者相枕藉”;
“十五年,泽州县复大旱,民大饥,疠疠死之如故”;
“十六年春,泽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户有全家殒没者”;
万历十六年后,疫情倒是缓解了一段时间,但到了万历后期,却再度开始肆虐。“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属县旱饥,九月疠疫,多喉痹,一二日辄死”;“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历正、二月犹不止。晋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历正、二月犹不止。晋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
……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朝末年肆虐陕晋、华北地区的那场大瘟疫,同样是从山西开始的。崇祯六年(1633年),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吕梁兴县)爆发鼠疫,兴县百姓为此逃之一空,随着兴县百姓的外逃,这次瘟疫开始迅速向周边扩散。
根据雍正年间《泽州府志》等史料的记载,同年泽州府和平阳府开始遭受疫情,在泽州府,“崇祯六年,高平、阳城、沁水夏大疫”;在平阳府,“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馑相望”。

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府县开始相继遭受疫情,“(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相较于陕西而言,山西各地的疫情自这一年后则更加严峻,例如大同府,“十年,瘟疫流行,右卫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十六年浑源大疫,甚有死灭门者”,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大同府仍是“瘟疫传流,人畜多毙”。而其他地区,也相继爆发疫情,灵邱“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半”,潞安(今山西长治一带)“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到河北,首先是河北大名府,“十一月……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河北地区疫情持续扩散,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顺德府“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顺天府的良乡县“瘟疫,岁大饥”,次年则“大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和前文提到的“疙疸病”,主要是因为腺鼠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症状,因此得名。

崇祯十五年(1642年),鼠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六年(1643年),河北地区的疫情依旧极为严重,如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 见则死, 至有灭门者”。
《明史·五行志》亦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次年,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前往天津督理军务,曾回忆京师的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在疫情继续肆虐的同时,腺鼠疫开始变异为肺鼠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天津的疫情同样极为恐怖,“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 哀号满路”。
这次鼠疫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地区极广,除了陕晋、河北地区外,河南、山东各地同样受到疫情影响,开封府阳武县、荥阳县、通许县、商水县,河南府的偃师县、阌乡县,彰德府,归德府,怀庆府,以及山东青州府,济南府的历城、齐河、海丰、德州、泰安等地同样遭受瘟疫肆虐。
鼠疫给明朝带来致命打击,成为压垮大明的最后稻草
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具体死亡数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估算,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仅陕、晋、冀三省的死亡人数便已经达到了上千万,仅京城的死亡人数便达到了二十万以上,大明京师不仅出现了“日出万棺”的景象,街道上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灭亡,固然有自身的问题,然而这场规模巨大的鼠疫,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不仅加剧了天下大乱的程度,更是对明朝的军事系统造成了致命打击。
最为典型的,便是名将孙传庭的阵亡,奉命率兵围剿李自成的孙传庭,本就被鼠疫横行、人死过半而头疼不已,结果朝廷方面还不断催促其出兵,以致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出战,最终战败身亡。

明朝末期,在卫所制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主要便是九边重镇,然而这场瘟疫却几乎彻底摧毁了九边重镇中的延绥、大同、太原、蓟州、宣府等镇。
结果,当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时,明朝不仅没有办法抽调兵力予以围剿,甚至在李自成率军自陕西攻往京城时,明军都没有足够的兵力予以阻挡,以致李自成除了在宁武遭到顽强抵抗外,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很轻松的杀到了北京城下。

与此同时,在鼠疫的肆虐之下,原本京师的十万驻军,只剩下了五万多人,而京营原本拥有的2.7万匹战马,也只剩下了1千匹可以骑乘。如此情形下,京军不仅丧失了野战能力,甚至连守城都变得捉襟见肘。当时,京师内外城墙有15.4万个垛口,而那五万从疫情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不仅“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大多身体虚弱甚至无法站立。
在闯军已经杀到京师城下时,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甚至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即便如此,城墙上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守城明军皆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在外援无法抵达的情况下,此时的京城实际上根本就守不住,因此守城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先后开城投降,闯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便攻破了京师。眼看大势已去,明思宗朱由检最终于煤山自缢,明朝就此灭亡。
-
- 杨广与李渊之间有何恩怨?二人是如何结仇的?
-
2024-04-11 21:33:29
-
- 同为汉景帝之子,刘荣和刘德谁的结局更悲惨?
-
2024-04-11 21:31:23
-

- 李光弼:能与郭子仪相提并论,为何却没他出名?
-
2024-04-11 21:29:17
-
- 上官婉儿是个非常有才的奇女子,为何她的评价却不好呢?
-
2024-04-11 21:27:11
-
- 明代宗朱祁钰励精图治,为何会被轻易推翻呢?
-
2024-04-11 21:25:06
-

- 为什么说高力士是千古贤宦第一人,宦官中的一股清流?
-
2024-04-10 20:53:02
-
- 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他的结局是什么?
-
2024-04-10 20:50:56
-
- 康熙时期的毙鹰事件是皇帝的自导自演吗?
-
2024-04-10 20:48:50
-

- 李隆基有多心狠手辣?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
2024-04-10 20:46:45
-

- 冉阿让是哪个名著人物(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跌宕起伏的人生 )
-
2024-04-10 20:44:38
-
- 文成公主是个怎样的人呢?她为什么远嫁吐蕃?
-
2024-04-10 20:42:32
-

- 淮西兵变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
2024-04-10 20:40:26
-

- 古代状元也是官职吗 高中状元会有什么样的待遇
-
2024-04-10 20:38:20
-
- 费祎被刺身亡,有哪些人有嫌疑?
-
2024-04-10 20:36:14
-

- 清朝皇帝赐府另居是什么样 仅仅是分家单过那么简单吗
-
2024-04-10 20:34:08
-

- 曹操为什么要杀陈宫
-
2024-04-09 11:07:19
-

- 娄师德为什么受人崇拜 他有哪些优点
-
2024-04-09 11:05:13
-

- 高仙芝被谁杀得?
-
2024-04-09 11:03:08
-

- 历史上潘安到底有多帅 李白是怎么描述
-
2024-04-09 11:01:02
-

- 司马错有哪些功绩 他的结局是什么
-
2024-04-09 10:5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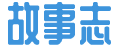


 英国历任首相一览表,英国第一任首相是谁?
英国历任首相一览表,英国第一任首相是谁? 日本最帅男星排行榜前十名(颜值惊艳的日本男明星名单)
日本最帅男星排行榜前十名(颜值惊艳的日本男明星名单)